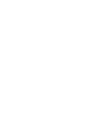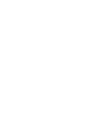新顺1730 - 第六七二章 猜疑链(中)
<script type="b404d5a37cf1fb0c5f7a5568-text/javascript">show_htm2();</script>
既然根本不相信吴敬梓的用意,或者根本不相信实践还有豫让之类的侠义,盐商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
原本只需要和朝廷斗智斗勇。
现在,则还是提防“后院起火”。尤其是提防刘钰借着改革为名,推动“验资买票”制度,让松江府的资本集团冲进盐业中来。
历史上,这些扬州的盐贩子,在满清赚了多少钱很难算清楚。但最常见的、也是很保守的估算,是五十年,2.5亿两到4亿两白银,纯利润。
盐业到底有多赚钱,这是不必说的。这么大一块肥肉,原本只有他们能吃得下,现在又多了一群虎视眈眈的人,处境何其难……
否了吴敬梓出的方法,这些人也只能采取他们最熟悉的办法了。
他们已经连试着变一变办法的能力都没有了,只会在他们熟悉的领域发挥过去的本事。
…………
“国公有所不知,世间都说,如今官盐甚贵,皆是大承包商的缘故。实则不然。”
“天下人多愚,只知其一,却不知其二啊。”
不久之后的海州城中,一个从扬州来的有些文名的说客,带着盐商们的意思和意思,来拜见了刘钰。
与时俱进,他们带了一个华丽的木箱子,里面装着从松江府银行那兑换的白银兑换券纸币,说是扬州点心。既没有送珠宝,也没有送奇物。
刘钰笑着说扬州点心其实挺好吃的之后,这说客才开始说话。
上来就来这么一套说辞,其实就是标准的尝试型行贿法。如果刘钰直接不接话,让他滚蛋,那就表明态度了。
同样的,如果刘钰继续让他说,那就意味着有戏。
在盐商们否了吴敬梓提出的办法后,并且要提防松江府财团插手盐业之后,想出的办法最终还是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他们的判断上——即皇帝想再多要点钱,但是之前修淮河已经要过一次了,皇帝有点不好意思拉不下脸来,所以故意让刘钰来吓唬他们。
实则,刘钰就是替皇帝要要饭的。
那么,要这么想的话,事情的关键,就不是道理了。
而是台阶。
讲的道理是不是真的有道理,意义不大。
关键是,讲的道理假装是个道理,做成个台阶就行。
所以才会选择上来就说到了盐政改革的关键问题。
刘钰没直接让他滚蛋,而且还笑着说扬州担心真不错,这就让说客看到了希望。
等这说客说完什么不知其二之后,刘钰轻捻了一下为了不让自己像东厂太监而留的胡子,慢斯条理道:“这盐政事,关乎国家财政。国家无钱,则如何安稳边疆?赈济水旱?”
“如今私盐泛滥,世人皆知由总商制度而起,使得官盐日贵。官盐贵则退、私盐贱则进,难道这私盐泛滥还有别的原因不成?”
那说客忙笑道:“国公,实不相瞒,这话看怎么说呢……”
“是。”
“也不是。”
“是,是说总承包商确实让次级承包商出过钱,真要这么说,那也没错。”
“但要说不是,事情也不能只看表面。苏子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反过来说,不入此山中,焉知真面目?”
“小人斗胆,请试为国公言之。”
刘钰轻咳一声,也不说话,只是慢慢饮茶。
说客见状,忙道:“确实,总承包商的确是问次级承包商要过钱,理由如国公那日在酒宴上说的那般:以各府州县缉捕私盐的犒赏花红为名。”
“但是,国公不妨这么想,如果不以犒赏花红为利,各府州县是否愿意出力缉捕私盐呢?”
“那些小贩子,只看了总承包商让他们出钱承兑,就说三道四、怨天尤人。”
“然而,若不努力稽查私盐,他们这些小贩的官盐又卖给谁呢?他们卖盐的时候,觉得好卖,所以看到总商手拿盐引,心怀嫉妒。若是盐不好卖,他们还会如此嫉妒吗?”
“可他们的盐好卖,不正是因为他们出了钱缉查私盐的缘故吗?”
“小人斗胆类比,若如国课征收。百姓觉得,凭什么要收他们的钱?可他们也不想想,若国不收课税,如何能护住边疆安稳?如何能保天下太平?难道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圣朝起于义军,终结乱世,恢复天下。是以圣朝以义治天下,禁宫匾额且有爱民之语。不忍加税于百姓,各地府州都无余钱缉私。”
“盐商出钱,做花红犒赏,严查私盐。”
“往小了说,那是为了维护小商贩之利,使得他们不至赔本。”
“往大了说,那也是为了朝廷能多卖官盐,如此才能多课盐税。”
刘钰心想扯淡,国课是不多,可地方税并不少。再说了,总承包商要钱,就只干了这个了?这真是标准的一堆屎里挑豆子,说这是一堆豆子。
他却也不如以前一般直接嘲讽,而是缓缓道:“如你所言,这些总承包商不但无过,而且有功?”
“小人不敢。若说问题,国公明朝秋毫、朝廷目光如炬,自然不会看错。确实,是有些问题的。然而,水至清则无鱼,况且人非圣贤孰能无错?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左传里的原话不是这样的,只是因为大顺毕竟要避讳,虽然之后也改了名,但“过而改之”这四个字牵扯的有点多,是以文人尽量避免。
说客见刘钰没有反对,又道:“国公可知,这票法实是出于无奈之举,之前才有试行的?如那福建等地,因着管束无力,而至晒盐泛滥。上不知出了多少盐、下不知道要缉多少私。”
“一开始,是按照盐田面积算,可后来发现这也根本不行,算不准。”
“最后,也就只能不得已而用票法。”
“可见,这票法一事,实非什么新意。只是前朝,乃至于更早,虽有票法,却也只是因着实在管束不了,不得已用之。”
“然而结果如何呢?结果就是闽、粤之盐,日日北进。三十年前尚在闽北为界,如今已至湘北、赣中。”
“每多一人买私盐,朝廷便少收几文银钱。而这几文银钱,打起来,便是一枚铅弹、一枚炮丸。”
“治国理政,岂可如那些腐儒所言?前朝教训,岂可不妨?这盐税是国家头等大事,若改票盐,只恐私盐泛滥,盐法败坏,以至于国家无钱可用。”
“而想要收的上盐税,小人以为,当于三处发力。”
“其一,便要控制盐场。取消长芦、福建、广东等地的晒盐法。各地百姓,一律如明初故事,以灶煮盐,不可晒盐。”
“如此,只要控制住了柴禾、盐锅,则私盐必少。朝廷便可复江西、湖南之失官盐之地。”
“其二,与四川各地盐场,加增灶柴税。蜀人煮盐,得天独厚,使用地气,不废薪柴。是以蜀盐价贱,往往有越界之举。”
“给蜀盐加薪柴税,朝廷即可收复楚之失盐地。”
“其三,所重之重,就在于缉私。重查、重判!”
“官盐所以难卖,皆因私贩太多。私贩之所以多,因为蜀、闽、长芦等地的盐,多以晒盐手段,价贱。”
“是以,治蜀、闽、长芦之盐,为治本。”
“而严查私盐,为治标。”
“此三种手段齐用,治标治本,又何愁官盐销售不畅呢?”
“若官盐畅,则朝廷税多。”
“朝廷税多,又可以给更多的银子查私。”
“查私越严,则官盐更多,又反过来促进了查私。”
“如此循环往复,才是真正盐铁手段!”
这话属实把刘钰给都笑了,心里实在是忍不住了,大笑道:“他妈的,那复井田、辟周礼,收天下之金铁而使百姓复用青石耒耜好不好啊?”
笑的同时,心里在想,果然是复井田周礼回三代之治的口号形成的习惯?改革的时候老想着跑步往回退?
说客见刘钰笑骂,自己却不慌张,他本来也没指望这话真的有人采用,只是为了引出来那个台阶。
刘钰笑过之后道:“你们啊,弄错了地方了。”
“首先,盐政改革,不是本官提出来的。是朝廷大臣提出来的,陛下只是差我考察一下,是否能变?变之利弊?”
“其次,闽、蜀……我管不到。陛下派我来,是考察两淮盐务的。我要听的是两淮的办法。”
“最后,明初时候,战乱多年,蒙元毁败,民生凋敝,百姓多亡。那时候行其制度,自大有道理。本朝起义兵,其缘由正是因为之前的制度与后来不甚适应,天数有变而人不知变,乃有天下将亡之祸。应运而生,此何意也?变以应天时,此真本朝之天命所在。”
“便如个娃娃,长到十岁了,你却偏要把他塞进周岁襁褓之中,此乱社稷之妄言!今日我不与你计较,日后慎言。”
警告之后,刘钰又道:“变法与否,不在于变,而在于为何而变?现在,私盐泛滥,官盐不畅,情况就摆在这。怎么变,那另有说法。你们不要给我讲这般道理、那般缘由。”
“我只问一句,你们准备怎么办?只说两淮盐,你们可有手段,保证朝廷盐税日增、私盐被打压?若有,那也可以说出来嘛。”
“总不能说一点办法没有,或是尽给出些往回退的办法,然后却只能嘀嘀咕咕地诅咒变法,半是诽谤半是挽歌。”
“你们可以提出来办法,只要可以达成打击私盐、盐税日增的结果,也可以按你们的想法变嘛。”
“对吧,现在变是共识,不可不变。”
“怎么变,才是关键。”
“你们老想着不变、不变,或者变人家蜀盐粤盐闽盐,你们这分明是搞错了方向。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今日我送你们一句话:怎么变,那是一个问题;变还是不变,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一个是可以解决的,一个是不可更改的。”
“现在票盐法就在这摆着,支持者就明说了,若行与淮北淮南,则每年增盐税50万两,且再无盐商拖欠积欠之弊。”<script type="b404d5a37cf1fb0c5f7a5568-text/javascript">show_htm3();</script>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