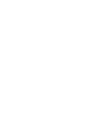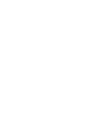新顺1730 - 第五零四章 阉党(中)
这些听起来完全就是扯犊子的谶纬之言,刘钰当然不信。田贞仪若是信,两人也根本不可能如此这般举案齐眉。
只是,他们自己不信,甚至可能朝中也没人信。
但是,要像是前朝那般搞穿凿附会、捕风捉影,搞个什么点将录之类的,大有可能。
而且“阉”之一字,本就不是什么好字。人家到时候就往自己这些人头上扣这么个大帽子,就凭那些人读书之多,还不简单?
最起码,对外一说,这群人是阉党,一开始可能只是儒林之中讲个笑话侮辱一下,可时间一久,怕这笑话就成了代号,顶着这么个名号那也着实不好听。
田贞仪说完这赤后、毛兽、白虎之类的谶纬之语,又道:“除此谶纬之外,夏政还有特点。”
“定府官,明名分,而审责于群臣有司:如今海军、陆军之军改;参谋部枢密院之建立,便应了此举。”
“主夏政而用兵者,讲究的是‘至善不战,其次一之。大胜者积众’。自三哥哥练兵以来,用兵之法,皆为夏政之风。”
“至善不战、其次一之。所说的,就是谋而后定,最好是不战而胜,其次就是一战解决。”
“平准噶尔之叛,孤军深入诱敌包围,阿尔泰山北麓一战而胜。”
“伐倭国之僭越,海军不战而胜,交兵不多,使得千秋僭越者一朝称臣,亦可谓至善不战。”
“下南洋、谋西夷,更是练兵十余载,以木马计夺锡兰、趁欧罗巴大乱攻荷兰、着罗刹国内讧谋西夷事。此皆至善不战之术。”
刘钰笑道:“这不是好事吗?”
田贞仪摇头道:“但是,然而,不过……这后面还有一句话呢。”
她顿了顿,在刚刚说完了一大堆的看似夸奖的称赞之后,说出了“但是、然而、不过”的后面。
“然……以春令而行夏政。”
“数战则士疲。”
“数胜则君骄。”
“骄君使疲民。”
“如此,国危矣!”
“以春令行夏政,所谓‘阉’者,便是这个意思。”
刘钰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想了一下朝中那群人的水平,搞这种事,比起田贞仪定然是不说是只高不低吧,但既田贞仪都能想到“阉党”这个名头,那些人真要是想要使坏,焉能想不出来?
这叫污名化。
阉党之前便已有之,天下都知道,这不是什么好话。到时候,捕风捉影地搞出一个阉党名录,穿凿附会,安上这么一个污名,时间久了,众人默认,着实难说。
先给人扣个帽子,尤其是这个帽子本身就是个污名化的帽子,这向来都是朝中争斗常用的手段。
朋党如此、阉党如此、东林……这就属于是后世污名化后,再把这帽子到处扣。而现在,阉党这名头,省了后世污名化的过程,早就污秽不堪了。
田贞仪见刘钰在那皱眉有所思,又道:“至于剩下两条,我也不必细说。”
“自唐设市舶司以来,再到三宝太监下西洋。市舶、海军、下西洋事,多以宦官领。”
“《通鉴》曰:唐置市舶使于广州,以收商舶之利,时以宦者为之。自三皇五帝以来,这市舶之事,起始可知的第一人,便是唐之宦官韦谋。”
“本朝自比李唐,又兴市舶海关。及至于明,三宝太监下西洋,更是将市舶、海关、海军等,与宦官阉人绑定了。”
“此其二也。”
“至于其三……”
“宦官阉人者,天下之边缘人也。被哂于儒林、不容于阴阳。”
“三哥哥与新学出身众人,或谈几何天文、或谈洋流海图、或谈贸易工商、或谈资本市场,亦与天下正学所不同。”
“宦官阉人者,以其身体而边缘;新学海军者,以其学问而边缘。”
“究其根本,恰可相似,谓之与宦官阉人一般不容于世、边缘于士,当可比拟。”
“此三论,污为‘阉党’,足以。”
说罢,田贞仪忍不住笑道:“况且呢,皇帝又说荀卿之四臣之论叫你们不要学,那不是要让你们做阉党,又是什么呢?”
“陛下既说,荀卿所谓的四种社稷之臣,都不要做;又盛赞米子明之‘内外有别’之说,其中深意,三哥哥可想到了?”
“内外有别,不是在赞米子明的南洋政策,其实另有所指——内外有别,你们不要想着当外臣,而是做皇家的家臣,此内外之别也。”
“前朝遗民黄宗羲曾言前朝宦官之祸,曰: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它无不皆然。”
“本朝以史为鉴,与天下之内,断不会行太监干政之事。”
“但于天下之外,分清楚内外之别……呵,三哥哥,我且问你:”
“这南洋、贸易之利……是归内库呢?还是太仓?”
“这南洋、东洋之政……是归六政府呢?还是归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看似权大却没有制度化的机构?”
“这海军、南洋的征战……是先由六政府、天佑殿廷议了呢?还是皇帝小圈子做出决断,以内帑、贸易公司为后勤,便出征了呢?”
“这新学、实学出身的人……可有资格选官为内地州县?可有资格与科举殿试大臣并列?”
“凡此种种,说你们是‘臣’,这怎么能对呢?你们不是天下的臣,而是皇家的家臣。皇家家臣,与天下之臣,是有区别的。这便是‘内外之别’。”
“而皇帝家臣,自古以来,难道不都是太监、宦官充斥吗?你们做着自古以来与宦官、太监等一样的事;行事风格与宦官、太监也是一样;不入朝堂、无有常设;所有权力,皆出于君恩私宠。”
“除了身体和宦官太监不同,剩下的,又有什么区别呢?”
“皇帝是要他们做皇家的家臣、家奴。不希望他们做真正的大臣。”
“皇帝希望他们知道‘内外之别’,有些事,根本不该是那些人该管的。”
“所以皇帝言荀卿之《臣道》,又言社稷之四臣不可学,更说内外之别为上善之言,便是再说这个意思。”
“只是,这话不好听,皇帝不便说,便让三哥哥来说。”
刘钰皱眉道:“内外之别?”
田贞仪点点头,补充道:“天下事,天下臣来做。天下臣,有道统。”
“本朝自改太祖‘均田免粮’之策,而行‘保天下’之名,便因着‘道统’二字。”
“三哥哥可明白,何谓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在于道统。”
“你们的‘道统’,不可用、不能用;但你们的能力很强,可以用、必须用。”
“宦官阉人,历来有能力的比比皆是,但有术而无道。皇帝用其术、用其能,又为家臣、家奴,便可避开道统之争。”
“朝中的事,要讲道统,要正道。内臣的事,不需要讲道统,讲正道。而且,内臣也讲不了天下的道统正道。”
“所谓内外之别,便是说,日后南洋、工商、贸易等事,不归天下事内。不归六政府、不归天佑殿,只是皇家私事。海军是皇家海军、贸易是皇家垄断之贸易、南洋是皇家之南洋。”
“天下的事,仍行春令之政,不变、宽容、妥协。天下外的事,争雄于西夷、夺利于南洋,所得之利,皇帝可以以私人补贴国库;反过来,争雄西夷、夺利南洋之辈,皆为内臣,不入朝堂,只是皇帝私属。”
“宦官不得干政、不得品评朝廷政策。让你干啥,你就干啥;不让你干啥,你也别大呼政策不对……既非天下之臣,便无资格论天下之政。”
“日后海外之事,为皇家私事,非天下事;既为皇家家臣,皇家要干,就干;要不干,就不干。”
田贞仪这么一说,刘钰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他一直以来都隐约觉得好像确实有这么一种趋势,甚至可以说从他练兵开始,就是类似这种趋势。
好处是,不用扯那么多的淡,皇帝支持,事就能做成。但坏处也多得是,不用扯那么多的淡的另一面,就是不是正儿八经的大臣。
念及于此,刘钰苦笑道:“看来皇帝巴不得我们都是真太监呢。”
田贞仪摇头道:“这倒不是。真太监,反而不好。”
“船山先生言:宦寺之恶,甚于士人,只因其无廉隅之借,子孙之虑耳,故悯不怕死。”
“真正的宦官,没有什么道德的约束、没有子孙家人的顾虑,所以做起坏事来,也根本不怕死。”
“海军众人,既有道德约束,又有子孙、家人的顾虑,做起事来,多有顾及。”
“因着学问为士绅之哂,边缘于世,是天下的边缘人。其实与宦官太监无异,却又没有宦官太监不考虑家人子孙、做事只需要考虑自己的不可控。是以真太监,反而不好。”
“如今这种局面,是最好的。但是,还需要一人点破他们的身份,告诉他们,别以朝廷大臣自居,内外有别,不过皇帝之家臣尔。”
“这里面,看似做的最好的,恰是三哥哥你。”
说到这,田贞仪再度掩口轻笑,这话听起来像是奚落自己丈夫“有做太监的天赋”似的。
刘钰看着掩口轻笑的田贞仪,无奈道:“我可没这天赋,怎么就做的最好了?再说了,这事儿我怎么说?”
“这些话,咱俩之间说说就罢了。难不成,真的去和他们说,让他们摆正自己的身份,学会当内臣?这性子烈一点的,谁肯受这番侮辱?皇帝肯定是想让我把话说明白,但绝对不想我说的这么直接,而且如此侮辱。”
田贞仪道:“此事,陛下既说荀卿之《臣道》,还需从荀卿之《臣道》中解答。”
“陛下说起那社稷之四臣,辅、拂二种,那是绝对不可以的。虽然荀卿多赞,但皇帝必忌讳。发动百官逼皇帝、违背皇帝旨意只要把事办成,这都是皇帝所不容的。”
“而谏臣,皇帝说箕子事,提及‘帝出乎震’、‘反客为主’二词。三哥哥也自思之,跑去殖民地施行心中的大道,将来反客为主,是否有这种可能?”
“甚至于就算是宦官,三哥哥难道忘了汉时宦人中行说‘必我也,为汉患者’之语乎?”
“但此四种社稷之臣中,皇帝唯一说的不甚担忧的,就是‘铮臣’。最多也就是感叹下,三闾大夫死了,于国无益;伍子胥自刎,吴国亦亡。但可没有担心他们有‘铮、辅、拂’之祸。”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