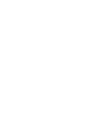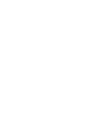-
向德明(尚书令),刘继昌(吏部尚书)、李继隆(枢密使)、慕容德琛(尚书左丞)、郭仪(兵部尚书)、寇准(迁都察使)、向敏中(迁财政使)、徐士廉(刑部尚书)、王钦若(中书侍郎),这九人乃是端拱元年初时,政事堂的宰相分布,也基本代表着整个朝廷的权力结构分布形势。
然而,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这个权力结构就支离破碎,这些站在帝国权力尖端的风云人物,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陆续离开,让出位置,交还权柄。
这是一个君进臣退的过程,整个过程谈不上平静,甚至本身就意味着混乱与失序,但事实上就是,政事堂的更新换代,一直很平稳,平稳到给人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这背后折射出的,自然是端拱皇帝低调而强大的掌控能力。
刘继昌、徐士廉二相公的倒台及去职勿需再言,端拱二年夏四月,乐平公、枢密使李继隆病逝于家中,结束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
李继隆毫无疑问是大汉帝国军史上一颗耀眼的明星,开宝-雍熙-平康-端拱四朝元老,时代洪流都冲刷不走他的光芒,而中流砥柱乃是他在康宗朝最恰当的评价。
他有一个不错的出身,年纪轻轻又受世祖大公主刘葭的垂青,驸马也没有成为他释放光彩、展现能力的阻碍,从戎几十年,西征北战,沙场建功无数,少有败绩。
李继隆一生是平顺的,光辉的,灿烂的,功成名就,几乎没有劣迹,完全是一个人生赢家的模板,是朝廷着力宣传的勋贵精英的典范,也是诸多功臣子弟崇拜的对象,即便是那些昏昏碌碌的膏粱子弟,其梦想着也希望活成李继隆的样子。
即便少不了人酸李继隆的出身以及驸马身份的作用,但谁也无法否认其出色的军事才干,否则,大汉功臣勋贵那么多,世祖的公主也不少,除了杨延昭外,还有谁达到李继隆的成就。
生前是完美的,死后,对于这个帝国功勋、大汉枢相、皇姑父,刘文济也给足够的哀荣。废朝,敕着神道碑文,进功臣阁,恩荫赏赐,这些都是应有之义,同时,刘文济还让李继隆配享太庙,追赠潞国公。
虽然给予了李继隆崇高的身后待遇,堪称人臣之极,但不得不说,即便李继隆不病故,他枢密使的位置也当不了多久。
从雍熙、平康到端拱,李继隆这个枢相,已经担任整整十年往上,虽说这个过程属于帝国特殊时期,并且在这个特殊时期起到了拱卫政权、稳定军队的作用,但于帝王,尤其是一个掌控欲强烈的帝王而言,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威胁。
大汉军制,枢密院虽然只有调兵之权,但结合李继隆几十年戎马生涯在军中积累的崇高威望,再加勋贵、驸马、四朝老臣、钦命辅臣这重重身份,结合起来所能发挥的威力,也是远超常人想象的。
在整个平康时代,帝国内外,有多少军队调动,都是李继隆主导的,又有多少弹压地方、剿贼平叛,出于李继隆的授意,这些都是说不准的。同时,若把那些旧事翻出来,严格依照条制来,一个逾制擅权的罪名是一点都不冤枉李继隆。
刘文济的心眼倒没那么小,他要针对的,不是李继隆这个人,而是这个人的身份并且处在这样的位置上,出于巩固统治、维护皇权的本能,他就需要采取一些行动。
而真正促使刘文济下定决心的,则是端拱元年李继隆怒讦徐士廉,致徐士廉及一批御史、言官逐贬地方之事。虽然刘文济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李继隆维护枢密院权威与军队利益的用心,甚至对徐士廉等人也存有看法,但他就是无法从内心释然这种被“威逼”的感觉。
有此一事,并且让他成功了,那必有二、三事,这是可作推论的,也不是一个志在有为的帝王能够容忍的。
刘文济性本沉静,登基之后城府就更加深沉,即便脑子里已经绞尽脑汁要换马,但面上一点也没表现,甚至日常间对李继隆也是各种体谅、慰劳。
而李继隆先于皇帝动手前的病逝,省却刘文济手脚的同时,也给自己留了个完美的生前身后之名,这或许也是一种时运。
李继隆既去,一场关于枢密使的博弈是免不了的,只不过这仍旧是军队体系内部的角力,准确得讲应该是军事贵族以及功勋将帅。其他人若敢染指,必遭反噬,即便皇帝也不敢贸然打破成行已久的潜规则。
不过,在端拱朝,真正能接李继隆班的,只有那么寥寥几人,最开始被列为公推人选的,只有郭仪、杨延昭、郭良平三人。
其中郭良平是争夺之心最明显的,作为第一枢密副使,他是距离这个职位最近的,年近七旬的他,没多少时间了,也等不了更久。
但同样,郭良平也是最不可能,甚至是第一个被排除在外的。不因他年老,也不是他功勋、资历不够,更不是因为出身不足,根子就在大汉军队的“陆海之争”上。
郭良平是帝国海军的旗帜性人物,在世祖的支持下,用实际行动将大汉海军抬到了不该到达的地位上,在其二入枢密院,担任副枢相期间,海军更取得了相比过去几十年跨越式的发展,包括南洋驻军改革、炮舰更新计划、训练升级以及远洋探索等等都是在他的主导下展开了。
在郭良平任职期间,帝国的海军腰杆是挺直的,声音是响亮的,但同样的,也达到了陆军老贵们所能忍受的极限。这个极限,也最多坚持到郭良平退休抑或去世。
当郭良平选择向枢密使发起冲击的时候,可想而知会遭遇怎样的阻力与攻击,这一点,他本人心里未必不清楚,但他还是选择出击,就像几十年前率军远航,将帝国触角延伸到波斯地区一般。
郭良平拼了一辈子,冲了一辈子,没理由在最后选择软弱,只不过,这一回,运势不在他,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倒在枢密使的权位前。并且在之后不久,就撒手人寰,享年六十八岁。
郭良平被排除在外,郭仪与杨延昭之间同样不好选,在世人眼里,这二人是最有资格担任枢密使的,毕竟是世祖时期的“勋贵三英”、“少壮三杰”,名望、履历、功劳都很扎实。
然而,郭仪本身就任兵部尚书不久京,已是宰相,不便轻动。杨延昭则已经退到侍帅这个“二线”职位上,另一方面,也跟杨业当初的扶持有关。
端拱二年的刘文济,已经彻底坐稳了皇位,已经不需要再想之前那般过分地小心翼翼,也能以一种自主的心态去决策军政。
对杨氏,他当然多有倚重,对杨氏子弟的提拔并无限制,但是对杨业、杨延昭二老,尤其是杨老太师依旧在世的情况下,让他把杨延昭抬到枢相的位置上来,他也实在难以安心。
那样,只会出现另外一个李继隆。
于是,在端拱二年仲夏新鲜出炉的大汉帝国新一任枢相,又是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扶风公、殿前都虞侯马怀遇。虽有些意外,但对于马怀遇,还真没法提出什么有效的反对理由。
李继隆、杨延昭身上的“buff”,除了驸马头衔没有,马怀遇都有,并且他曾是世祖养子,与太宗的关系更亲如兄弟,只不过,履历与功劳上不如李、杨那般耀眼罢了。但是,他担任枢相,还真就没什么人能挑战得动。
尘埃落定的同时,也附有皇帝一番安抚操作,杨延昭晋崞县公,使杨氏一门两公。郭仪则晋一等武进侯,为郭氏再开一脉。
此事后不久,致远侯郭良平也郁郁而终。空出来的第一枢密副使的位置,皇帝刘文济在善加斟酌之后,选定侍卫司都虞侯曹玮,这是已故真定侯曹彬第四子。至于腾出来的侍卫司都虞侯,这个实际掌握侍卫马步军统兵权的要职,刘文济则敲定护圣军都指挥使田邦义。
此人乃是功勋老将田重进之孙,虽同属于勋贵,但家室就不那么耀眼了,与杨、李、曹者相比,暗淡的不是一星半点,当然这也是刘文济选其掌握兵权的主要原因之一。
世祖、太宗是何感触不得而知,但经康宗之荒后,轮到刘文济当家做主,他对朝野上下,尤其是军队之中,那强大、固化的军功贵族阶级,难免带有戒心。
刘文济自是知晓军队不可轻动,勋贵的核心利益不易侵犯,因此,大动作可以按捺,小刀子却可以慢慢地割。先在军功勋贵集团内部搞分化平衡,提拔如田氏这种势力不强、影响力相对局限的勋贵家族,后面再培植庶族寒门将领,当然这注定是个漫长的水磨工夫的事情,急躁不得。
另一方面,在对军政令系统做“小手术”式调整之后,刘文济又下诏重新设立枢密直学士一职,以内阁学士、知制诰曹利用充任,重置的理由则是他不通军务,但军国大事,不能不熟悉,因以此职作为皇帝与枢密院之间联系的桥梁,加强沟通......
一系列幅度不大,但显着加强皇帝权威动作下来,包括文官系统内一些眼光毒辣的人,都察觉到今上那颗并不端拱的心,而对此感受最为深刻的,毫无疑问乃是军队体系,尤其是军功老贵家族。
不过,军队里的实权派们,却并没有就此表示些什么。帝国军制,给了他们近乎超然的地位与待遇,同样对所有人也都有一套摆在台面上的限制,台下怎么做是一回事,但谁敢在台面上搞形成规则共识的事情,则将面对来自上下的挤压。
另一方面,刘文济的系列操作,也都在既定规则之内,并没有动摇勋贵们对军队的主导地位。总不能期待每个皇帝都如康宗一样吧,而由平康时代走向端拱时代过程中产生的不适感,所有人都得慢慢接受,并且,是臣子去适应皇帝,这是由强势皇权决定的。
端拱三年春,许昌王、中书令刘曜上奏,安南王刘文涣薨于交趾。
刘曜,世祖皇帝幼子,母周宜妃,生于开宝十九年,初封韩公,康宗继位后晋爵许昌郡王。前者,以刘继昌落马遭贬,依常例选宗室入政事堂。
皇帝刘文济二请赵王刘昉出山,仍为其所拒,又邀掌管宗正的燕王刘昭,不出意外,刘昭也选择婉拒。二王悉拒,不得已之下,刘文济只能把目光投向其他人了。
世祖诸子,除了赵、燕两大亲王之外,在京的只剩蜀王刘晅以及许昌王刘曜了,最终,在一翻考察之后,刘文济敲定以许昌王刘曜入政事堂,拜中书令,同时监管理藩院,除了平衡朝局之外,主要搞外交,尤其是与四方封国、藩属之间的交往联系。
“安东事件”仍未调查清楚,但不论真假如何,都给了刘文济一个警醒。随着这一年加强对各藩国的关注,获取众多政治、军事、经济情报之后,刘文济也意识到,血脉相连的帝国与诸封国交流频繁,但正在往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发展。
这种趋势,作为中央帝国的皇帝,刘文济心中很膈应,那是一种事务脱离掌控的不适感,但是面对这种趋势,他又不得不冷静下来,审慎分析,理性对待。
封国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但域外封国,却仍是一个新鲜事务,也需要一种全新的方式去相处,若宥于旧眼光、老故事,必然会出问题。
安东国状况不断,就是一种极其明显的征兆与体现了。事实上,刘文济心中也清楚,中央帝国与诸大小封国之间关系往来,必需有一套更实际、更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规则办法,使之走向正常化,否则,只会在越来越多的矛盾与拉扯中,渐行渐远。
地域上的距离,本就让世祖之后皇室宗亲间的情分难以长期保留,利益二字或许冰冷,但对双方而言,却可以让各自冷静理性地对待双方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份关系的发展走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以帝国中央的意志为主导,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刘文济对许昌王刘曜的委任,是寄予厚望的,实权也很重,同时,刘曜的年纪(比刘文济还小五岁)足以陪他一起构建一套更进一步的新宗藩体系。
当刘曜向刘文济汇报安南王刘文涣之薨时,也是一次对尚在形成中的“新宗藩体系”的实践机会。不过在此之前,礼节人情还是要先讲的。
回京夺位失败后,刘文涣于端拱元年初夏,便再次黯然离京,南归封国。在途中,就染上了肺疾,回到安南,久治不愈,终于三年春离世。
刘文涣的一生,多少带着些悲情色彩,他出身高贵,才智不凡,胸怀大志,或有孤傲之时,少有松懈之日。少年时期,是世祖疼爱的千里马,青年时期也是太宗寄予厚望的皇长子,只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遇人不淑,宏图大志,尽成一空。
当然,刘文济这个对手对他的影响,比表面呈现的要大得多。虽然他们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直接面临竞争,但一出手,就直接踩着他的肩膀登上至尊之位。
悲情固然难免,但堂堂的安南王,也难让人同情,因为天下没什么有资格去同情他。人生最后的一年多,虽然饱受病痛折磨,但大抵也是刘文涣活得最清醒、最从容的一段时光了。
临死之前,刘文涣还将后事安排好了,立四子刘继丹为嗣,继承王位,同时以王后刘娥监国。刘文涣一共有四个儿子,常妃所生的刘继元、刘继初,毫无疑问被排除在候选人之列。
剩下的只能从三子刘继诚与四子刘继丹中挑选,二人年纪都不大,一个十四,一个十一,最终选择了刘继丹,因为他无母,王后刘娥的枕边风厉害。在刘文涣养病的这段时间里,安南国很多事务,实则就是刘娥在帮忙处置,并且处置得不错,优秀的政治能力让刘文涣意外之余,也促使他做出了最终关乎安南国命运的决定。
而依封国制,刘文涣的这些安排,还需上表京城,请中枢朝廷确认,批复授册,遣使宣告之后,方具备法律效力。
为此事,刘文济还专门召集政事堂诸宰,举行了一场廷议,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倒也没有太大意见,安南王的决定总还是要尊重一二。唯一的异议,只在王后刘娥监国的问题上,经历了慕容太后干政甚至仍在经历着的大汉宰相们,对“牝鸡司晨”这种情况格外看不惯。
然而,仔细斟酌下来,却又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办法,总不能把安南这样的“大国”,直接交给一个11岁的娃娃吧,再不乐意,也只能捏着鼻子先认了,等刘继丹长大,再作区处。
寇准对安南还是很有感情的,他单独面圣时,向刘文济提出另外一个处置办法,将安南国收回,重归中央直辖。然而可以想象的,刘文济断然否决,分家容易,合家难。即便不考虑其他影响,刘文济不能不顾虑世祖、太宗分封之政的强大影响力,这份影响来源于诸多既得利益者的强力维护。
最终决定,照准安南所表,以集贤殿大学士、礼部侍郎杨亿加安南宣慰使衔,南下交趾,代表朝廷进行抚慰,立新王,授金册。
这同样是打破常规的一个举措,因为按照最初的制度,封国王位世袭,新王需要亲自到京城接受册封。这种做法,体现的是制定此等规矩的世祖皇帝的强势掌控之心,但在端拱三年,显然早已不合时宜,因而做出一些顺势的改变,也是理所应当。
从此,帝国中枢开始正式转变对各封国关系政策了。于安南国而言,随着新王刘继丹的继位,也开启了一段错综复杂、斗争频繁的混乱时期。
王太后刘娥的执政,注定充满了挑战与困难,后宫有赵太妃不甘寂寞,在朝有赵氏家族及刘文涣心腹旧臣们,同时,国内有诸多叛服不定的蛮夷之属,饱受白眼、心怀怨愤的刘继元、刘继礼兄弟也对失去王位耿耿于怀。(这两个儿子,刘文涣感情很复杂,将其远远地安排在西南的文州与万州镇守,眼不见为净。)
诸方势力,种种矛盾,在没有刘文涣的强力支持后,刘娥的摄政之路肉眼可见的艰辛,而他能依靠的力量实在不多,唯一的优势就在于,前后先王遗命,后有朝廷敕旨,并且牢牢地将新王刘继丹置于羽翼之下......
ps:在收到刘文涣去世的消息后,刘文济曾大哭一场,长大成熟后的兄弟俩,渐行渐远,那是时局的推动,历史的选择,但曾经有那么一段日子,兄友弟恭,一同环抱世祖之膝,欢声笑语。
与康宗刘文澎,二人或许都有一定代沟,但二人之间,却总是有一份兄弟之情。如果刘文涣活着,那么“各自安好”,待其薨,有些情感也就压制不住了。
太宗皇帝拢共就三个儿子,如今,三去其二,并且都是英年早逝,这同样给刘文济带来不小的心理压力,也促使他做出了早立太子之决定。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