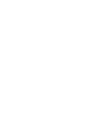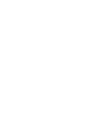镇国公主[GL] - 镇国公主[GL]_分节阅读_269
镇国公主[GL] 作者:允
镇国公主[GL] 作者:允
婉儿不语,只低头将衣裳合上,不让她看,她便更心虚了——她自得了此症,便没叫婉儿碰过中衣,心头有事,亦不曾关注过婉儿——眼在四处一扫,瞥见远处案上有笔墨,忽地生出个主意,迫不及待地起了身,走到案前,只见黑墨、白麻与两只细笔,婉儿怪她行止,跟在身后叫“陛下?”,她不理她,忙忙地在四处翻了一阵,幸而竟寻出了一套辰砂。自用水合了砂料,提笔蘸朱,在掌心试了几次,调得刚好,方指着自己的坐席向婉儿示意:“坐好。”婉儿待要推辞,已被她压着坐下去,她一手揭开了婉儿的衣襟,眯起眼睛点了丹砂,在胸口那处细细描绘:花心、花丝、花瓣。勾完又以墨汁沾在边上,勾出一点花萼。
她的画艺不及字法,却也算不上坏,一笔一划悉心勾勒毕了,眯眼一看,也有几分神似,再提笔又在另几处也画了花朵,再以绘以墨汁,竟成了一枝梅花,她有些得意地将这一幅画看了又看,引着婉儿到镜子前展示:“如何?”
婉儿先是红着脸,对着镜子看了一阵,忽又顽皮地眨眨眼,自案边取了笔,点了朱砂,伸手去掀她的下裳,两眉微抬,两眼微斜,面带问询之色,她迟疑了片刻,终是轻轻地点了点头,偏头斜看,见镜中的婉儿贴着她半跪下去,脸凑在她的大腿处,手执笔墨,一板一眼地在她腿上勾勒出两朵各逞风情的梅花,画完对着吹了许久,候墨迹全干,方扯着她转过身,面对镜中,指着自己胸前与她腿上轻笑:“虽未能共赴长生,却同生了长生之病,又同得此长生不败之花,岂亦非幸事?”
镜中梅花如两丛并蒂高低相依,她望着这梅花,伸出手去,搂住婉儿,低声一笑:“若如此,不如叫人替我们两个写一幅真,人虽不能长生不死,画却能长存世间——如何?”
第397章 行露(二十五)
佛奴自丽春台回来了, 韦欢故意留他在外候了些时候,自在内换了一套鹅黄轻裳, 挽了个不高不低的发髻, 方将人叫进来:“她怎么说?”
佛奴小小地一弯腰:“公主说知道了。”
韦欢忍不住道:“就这句?”
佛奴忙跪下去:“就这句——小人一得吩咐便去了丽春台, 内外与平时无异。顾九曲与四五个人躲在东庑廊中吃茶点,见了小人, 亲自回廊引进去,交在内殿外,内殿只仙仙娘子一人听候吩咐,便引小人进去。公主独自在窗边立着,像是在想事情,听了报,笑一笑, 说:‘知道了’,命仙仙娘子带小人去吃果子,仙仙娘子亲将小人引出内殿门, 交王团团、杜曲曲两个在西廊小屋和小人说话,备了四样点心、一壶茶, 赏了一串新钱,小人分与王、杜二人,点心也与她们同吃了, 问她们公主起居,只说很好,小人还特地候了一刻, 见公主确实再无其他吩咐才回来。出门时候顾九曲叫小人,说内殿早晨便吩咐宫门备车,许是要出宫。”
韦欢点点头:“她赏你多少,你自向王德去报,双倍给你。”听佛奴道“小人为娘子办事,并不图赏赐”,便笑:“正因你忠心办事,所以更不能亏了你。”斜看他一眼,笑道:“你那结义阿兄,前些时候因私下樗蒲赌钱被巡检拿到?你没被发现罢。”
佛奴面上变色,叩首道:“小人实不知此事。”
韦欢轻笑:“他们报到了我这里,我想喝酒樗蒲之事,宫中虽然屡屡禁止,毕竟人情所在,偶尔为之,倒也没什么,且陛下崇尚佛理,务在宽仁,我们自当秉承圣意,体从天心。故已命他们从轻发落,明日判文即出,你今日可先去探望探望他,亦可稍慰兄弟之情。”
佛奴大喜:“娘子再造之恩,小人与小人阿兄没齿难忘,小人这就去和阿兄说,叫他自来拜谢娘子。”叩首而去,感念不止。
韦欢待他去了,才垂下手,向镜中自己一望,半晌后立起身,步行至正殿,执事人等具在,有只拿了手札、帖子的,有特地拿了疏子的,一一恭候她的示下,武氏自闻传声时起便起身弯腰迎候,至她坐定、示意方挨着杌子坐了——她素日话便不算太多,今日便更少,韦欢以事询她,都只道“听二娘子的示下”,韦欢益显慈和,加意多问她的意思,凡她所言,无有不从,六尚体韦欢之意,亦甚恭顺,一日要务,顷刻毕结,并无二话,韦欢起身时众人又皆垂手躬身相送,步至庭中,又有皇帝遣宫人赐菜——不过两样平常蔬菜,亦非专为皇帝所备之特膳,与平日例赐宰相、国夫人之具等同,于韦欢却是头一次,殿中人皆欢欣鼓舞,韦欢亦少不得口衔谢辞,重酬天使,领着人恭恭敬敬地将这两道菜迎进去,盘盏毕竟,次后重又更衣整容,携守礼往绮云殿问候起居,在门外候不至一刻,便见太平着蜀衫短裳、蜀锦绸袴,扎着头过来,见了韦欢,方拱手一礼,已有内人引她三人入内。
正殿中人头攒动、衣冠交错,诸武之亲眷毕集,具来为皇帝贺寿,武三思、武懿宗几个半跪在席上,樗蒲为乐,皇帝倚坐榻前,靠着婉儿,边与诸公主、夫人们说笑,边看子侄们赌钱取乐。
太平已算是来得晚的,韦欢却该算是不速之客——韦欢略有些不自在地动了动,手却被太平一把握住,太平携着她大步上前,笑嘻嘻向皇帝道:“阿娘好偏的心,自己在这里设宴取乐,不叫我也算了,分了菜出去,赐了阿嫂,却不赐我。”
韦欢竟不知皇帝并未叫太平,膳房亦未闻皇帝有宴乐事——不过御膳无定时,尚膳又归诸武把持,她不知也不为奇——微垂了眼,随太平上前,听皇帝笑道:“不是宴乐,不过因他们过来看我,顺便掷双陆、打樗蒲,乐一乐罢了。宫门上说你备了车出去会人,所以没有叫你——怎么这副打扮?”
韦欢心中一动,抬头去看太平,这小娘骨都了嘴道:“我人分明在宫里,何曾要出去?本来是见天气晴好,想叫人蹴鞠的,寻人时一个都不在,宫里问了个遍,才知都在阿娘这里,路上又见向阿嫂那里送了菜,以为阿娘想得到我,满心欢喜地回去,等来等去没见个消息,我想素日阿娘有宴,就算不叫我,也总要赏些饭菜,什么都没有,是不是近日有什么事做错了,阿娘生我的气,所以不愿理我?若是这样,也不消阿娘骂我,我自己就来向阿娘请罪啦——但求阿娘赐谕,使儿明白罪在何处。”一面说,已赌气跪了下去,膝行至皇帝身前,抱住她的腿。
皇帝笑道:“你这小机灵鬼,口口声声说是请罪,一面问‘罪在何处’,倒是好意思么!快起来,这么大人了,不许作这磨磨蹭蹭的样子。既已来了,便一道和兄弟姊妹们好生玩罢,阿韦与大郎也坐。”
太平偏不依,仰着头道:“我明明没出去,谁说我出去的?还要会人——谁都知我一向不好交游,所亲近者,都是宫中妇人,出去和谁相会?宫门上谁乱说的,叫他出来,狠罚几十杖才好。”
殿中喧闹稍减,武三思与武懿宗都停了局,抬头来看这边,韦欢看武懿宗满头是汗,心中有了计较,悄没声地退开一步,又向守礼使眼色,守礼看看太平,不甚情愿地退开一步,挨在韦欢身边。
皇帝没留意这边,缓缓坐正,伸手抚了抚太平的头,有些尴尬地道:“不是什么正经回报,是你河间王兄听宫门上说了一句,便随口告诉朕了。”
韦欢眼观鼻鼻观心,听太平道:“那更该罚了——监门卫掌宫掖门禁及守卫事,身系天子安危,怎可轻易将宫中行藏告知外人?河间王已罢了左监门卫将军的职,怎可打探宫禁上的事?”
太平学了她用过的手段,韦欢竟微微有些得意,见皇帝面上变色,武三思与武承嗣都端正跪定,要替武懿宗辩解,抢上前一步,挽住太平的手,含笑道:“阿家大病初愈,又正是阖家团聚的大好时节,何必汲汲计较于这些琐碎事,以此搅扰阿家的雅兴?”
眼看二武还要开口,连武懿宗也缓过神来,开口叫了一句“陛下”,又笑命人道:“再拿一副双陆,我与公主下一局。”
皇帝默不作声地看了武懿宗一眼,将太平自地上扯起,半笑不笑地道:“你河间王兄一贯糊涂,你又不是不知道。罚他为你执杯倒酒,这事就算了罢。”
作者有话要说: 明天更新稍晚点,应该在晚上12点前。
第398章 内宴
说来奇怪, 在我和阿欢争执之先,朝臣们对皇太子到底该是李旦还是李睿并无争执。在他们眼中, 首要的目的是光复李唐, 似乎只要是姓李的、男性的人做了皇帝, 无论这皇帝是谁,资质又如何, 根本就不重要。但是在我们争执之后,局面忽地有了微妙的转变。原本大部分唯李旦的名义是从、为李旦的婚姻学业僚佐等事据理力争的大臣们像是突然想起来母亲不止这一个“孙子”,狄仁杰在台省“偶遇”了我,“顺带”地提起了守礼的亲事;御史李昭德上疏,请母亲不吝土地、分封诸孙;新召回至都的杜景俭请为李彬诸少子赐婚、使皆出阁;而王方庆则借着母亲戏语问他“君竟忍心将长子判官至眉州”时断然回了一句“陛下之爱子尚在庐陵,臣之长子如何不能在眉州”。
我不知他们对李睿的拥戴到底有几分是出自真心,然而李旦远不及李睿名正言顺是不争的事实, 我虽已对阿欢放出大话要助李旦,但心里对这事究竟有几分能成、以及李旦上台之后李睿一家该当如何却全无把握,实在计无所出, 只能一面隐晦地教李旦讨好母亲,一面托人向崔明德送信询问, 崔明德倒是尽可能快地回了信,怕无法安全送到,托在家书中给了崔秀, 崔秀则约我在长乐观中相见长谈——今日打算出宫,本是为此。
然而一早便先是遇见佛奴传信,说起和尚的事, 接着又有婉儿的信来,说起这一场随兴而起的内宴,以及武懿宗无意间提起的我要出门“会人”的事,于是出宫之事作罢,我特地换上了轻便的家常衣衫,笑着去了绮云殿——母亲年老倦怠,不爱穿繁冗常服,在婉儿处尤其如此,诸武既是进宫庆贺,必然衣冠整备,我若于一众衣冠间独着短衫轻衣,便是与众不同的亲昵,比起诸武,更像家人。
阿欢未必知道绮云殿之事,却也不约而同地穿了家常衣裳:浅紫短衫、浅绿间裙。携着服浅绯、系玉带的守礼,不至于过分素净惹母亲不喜,却也不至富贵招摇如武承嗣。
她察言观色的功夫着实是第一流,只听我说了几句话,便轻轻巧巧地接过了话头,堵住了诸武为武懿宗辩解的路。从此不但河间王“糊涂”的名声坐实,母亲心中也当种下芥蒂——一件小事不怕,两件、三件、四件也不怕,怕就怕在长期累积,积毁销骨,而这样的细小事,母亲都已打算让它过去了,旁人也不好特地再提,更无从辩解,久而久之,聚沙成塔,众口铄金。
武承嗣想这样扳倒我,而我也打算这样扳倒他。我不知他对我的动向究竟能了解多少,早上所谓“会人”是随口污蔑竟至成真,或是凭借蛛丝马迹抽丝剥茧,又或是直截便在我身边有亲近的人——最后一种可能性倒是不大,毕竟我身边的人不止经我筛选,还有阿欢和母亲把关,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向母亲显示这一种可能,毕竟我现在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宫中,窥伺于我,便是窥伺宫掖,母亲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事在她眼皮底下发生。
我从头到尾都噙着笑,陪着母亲竟了这一场内宴——初时的确不是宴会,不过是武承嗣和武三思讨母亲的好,说要家人一聚,陪姑母说说话,后来阿欢和我凑了各热闹,母亲干脆便又四处叫了人去,安定公主、李旦、李德、李友…凡武李两家的亲属,甚而杨氏、郑氏中紧要的几位都请了来,内宴之所也自绮云殿移去了飞香殿,叫尚膳临时整治了许多肴馔,取出一坛一坛的御窖美酒,自明至夜,人人尽欢。
我已渐不耐熬夜,这一次却强挺着全程陪侍,母亲到二更时掌不住,起身去偏殿小憩,才一动作,安定公主、阿欢与我及武承嗣之妻便都向那边去,因我离得最近,到底占了便宜,与婉儿一左一右地扶持母亲而去,婉儿取水为母亲擦拭,我便为她脱鞋除袜,母亲半梦半醒之间将脚伸出来,在我肩上一划,轻笑着道:“阿婉。”待见了婉儿拿手巾过来,低头将我一看,却又笑道:“是太平。”
我不动声色地直起身,躬身道:“阿娘。”恐母亲尴尬,忙低了头不敢去看,母亲却大大方方将我扯到榻前坐下,又招婉儿与我并坐,一手支颐,将我们看了又看,我见她醉眼迷离,大胆问道:“阿娘在看什么?”
母亲笑而不语,一手伸出,婉儿立刻接住,搀她起身,盘腿坐于榻上,一手搂了婉儿,一手搂了我,笑道:“你二人,年岁相近,志趣相类,又同无夫婿子女,当相友爱。”
我笑道:“那必然。说来上官承旨还曾教过我,算是我的师傅。”
母亲摇头笑道:“又没别人,不必和你娘说这些虚话。”我见她坐着时都摇摇晃晃,已是醉得狠了,忙道:“阿娘歇一歇罢,养足精神再和儿掷骰子去,不然儿胜之不武。”还要向婉儿递眼色,婉儿却不待我说,便已起了身,扶着母亲倒下去,又替母亲盖被,母亲斜眼看她,嘟囔一句:“热呢。”被婉儿一看,便又不提,却道:“你不要坐在地上,坐上来。”
婉儿看我一眼,依言挨着榻沿坐着,我见不是自己久待之所,忙便告辞,将出门时,母亲又在榻上闭着眼道:“望日大朝,你随朕同上朝去。”脚步一顿,在门边拿眼去看婉儿,婉儿向我摇摇手,我便告退出来,重回宴中,心头猛跳不止,举起酒杯,一气饮了半杯,才稍觉镇定,一转头见阿欢执盏前来,向我一碰杯,笑道:“二娘闻知了什么好事,笑得这样灿烂?”
一句话说得诸武兄弟几个都偏头看我,武三思举杯近前,笑向我道:“方才是我的不是,十二郎不过偶然听说,和我提了一提,不合我听姑母说要叫你,恐中使白跑一趟,惹她老人家不高兴,多和姑母说了一句,在此向表妹赔罪了。”
他身边武承嗣与武懿宗俱是面色阴沉,却也向我一举杯,阿欢笑道:“都是自家人,二娘想是不会计较。”
我亦笑:“那自然。”与他们三个一一碰杯,隔了一会,又重向武承嗣、武三思两个敬酒,并与几位王妃敬过,阿欢亦领守礼向诸武作兴一圈,坐在几位王妃中亲亲热热地谈起些面脂、口脂、经讲、叹佛的事,守礼独坐无趣,挪到我这边,和我闲说了几句话,我见他说话心不在焉,似有心事,故意套问几句,问他在军学中如何,又说起他近来的实验,他果然便渐亮了双眼,片刻后,借着话引,扭扭捏捏地向我道:“姑姑…守礼想求姑姑一件事。”将坐席稍挪近一些,低声道:“姑姑前时找来炼丹的那些人还在么?能不能借我些时候?”
我心中一沉,抬眼仔细打量他:“你要这些人做什么?”
守礼没察觉到我的目光,扯着我的袖子笑道:“姑姑不是说炼丹可以做‘火药’?我在军学里试过几次,但因实在不谙丹事,所以未能克成,要是有些懂丹的术士来帮忙,说不定能研制出来。”天真地抬头,眼笑盈盈地看我:“边关正在打仗,独孤师傅也在前线,若能有这东西,想必不会再有那么多将士牺牲。”
作者有话要说: 在车里码出了这一章,于是并没有很晚更新O(∩_∩)O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