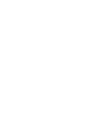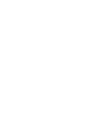镇国公主[GL] - 镇国公主[GL]_分节阅读_236
镇国公主[GL] 作者:允
镇国公主[GL] 作者:允
母亲挑眉看我,我略抬了头笑:“儿斗胆说一句话,阿娘不要生气——阿娘父承武氏,嫁与李氏,虽登基御极、改易江山,名为武氏之主,其实还是身兼两姓,日后无论传位于何方,另一方都难免有屠戮之灾。儿倒不为哪一氏说话,然而一面是阿娘亲生血脉,一面是阿娘的宗族血亲,无论哪一方受难,都绝非阿娘所愿见,不是么?三郎是李氏宗子,魏王是武氏宗长,他若能与三郎多加亲近,两姓结好,绍绪万代,方不负阿娘之心,阿娘觉得如何?”
母亲露出深思的神色,偏头看我:“我本以为…你不大喜欢你的表兄们。”
我笑:“阿娘是因我不愿嫁给他们,所以以为我不喜欢他们么?”
母亲不语,我道:“倒说不上不喜欢,只不过…原本阿娘只有二郎、三郎和我,忽地又多了这么多侄子承欢膝下,分薄宠爱,说我不计较,当然是假的。可他们毕竟是阿娘的侄子…而我是阿娘的嫡亲女儿。血脉之亲,不唯在父亲,亦在母亲。何况父亲可以有众多妻妾,生许多儿女,母亲却只有一位丈夫,所生不过我们几个。于我而言,阿娘的亲属,亲近尚胜于阿耶之近属。”
这不是我头一次说这样的话,然而母亲却似头一次认真听我说一般,静静看了我一阵,半晌才道:“兕子告诉阿娘,这究竟是你的真心话,还是哄阿娘的?”
我笑道:“阿娘不要怀疑,这的确是我的真心话。时人都以父为尊,宗族传承,总在父亲那一边,是故中表多有婚约,同姓反倒不能成亲。可仔细想想,单以血缘而论,中表之亲,与同宗之亲,又有什么区别?同样是传了父母一半的骨血,远出一服,则淡一半,如此而已。以父亲论,和以母亲论,又有何差?倘若异位而处,以母为尊,则表兄们反倒是我最亲近的人,同宗中除去二郎、三郎,旁的倒是远亲了。阿娘是前所未有的女皇帝,颠覆了千百年男人在上的传统,我私心里一直崇敬着阿娘。阿娘虽不能改变这以父为尊的世道,可我却一直将阿娘当做这家里的主心骨,与其说我亲近表兄们,倒不如说我亲近阿娘。武氏也好,李氏也罢,哪怕是郑氏,于我其实又有何相干?我只是阿娘的女儿,也只想做阿娘的女儿。”
母亲绽出些笑意,却又一叹,伸手在我脸上一拍,轻轻道:“这些话止于你我,以后…不要再说了。”
作者有话要说: 注释:
1.古人以同宗为亲人。父亲的亲属是“自家人”,母亲的亲属是“外人”,所以同宗之人,三四代外,还是亲戚,可母亲那边往往只要一两代外就不亲近了,而且同宗之间不能成亲(最早同姓就不能成亲,偶然破例的会被议论,到唐代娶同姓之女的人依旧有被鄙视的),而母亲的亲戚却可以随便嫁娶,因为是“外人”。现代的基因、血缘等理论,回到古代就是谬论。
2.关于剖心,古人因为医学知识的缺乏,加上忠臣孝子之类的神奇事迹广泛流传,因此深信一些化血成碧、挖心剖腹之类的传闻,历史上则天就因安金藏剖腹明志而大受震动,免去追查李旦谋反之罪。但是事实上未受过系统解剖训练的人应该是剖不了自己的心的(经某医生读者指教),尤其是在医疗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另外中古时代还不像后来“尸谏”那么流行,因此一旦有些比较惨烈的言行,就极易触动人心。对则天这种相对开明愿意纳谏的君王来说更是如此。
第342章 风力
自集仙殿出来后我下意识地便想向百孙院去, 想了一想, 却依旧是回了丽春台。前夜我几乎一夜未睡, 昨日清晨便出宫回家,一日忙碌, 未曾间歇,夜里亦不曾有分毫睡意, 这一时虽精神尚好, 却总觉得应该歇上一歇,免得将自己累出病来,反倒误事。
白日里果然比夜里要好睡些,我不知不觉便在殿中睡到了午后,醒来时还懒懒散散, 不大想动弹,在床上翻了一圈, 听见仙仙过来叫我“庐陵王小大郎在外等候了许久了”,方自床上挺身坐直:“他怎么来了?”忙忙起身穿衣,仙仙一面助我穿衣, 一面道:“说是来探病的,一定要等到娘子起身,我们只好请他在偏殿坐着,拿了娘子上回命做的七巧板什么的给他。”
我看一眼天时,又问:“可留他用了饭?”
仙仙点头:“周娘子亲自下厨,做了几道小菜,还有娘子素日想出来的那些小点, 什么鸡翅、牛肉丸、奶茶,都有。”
我本已将衣裳穿好,预备出门了,听这话又一转头:“午饭就午饭,上这么多乱七八糟的零食做什么?小孩子嘴馋,养成坏习惯,以后只吃零食,不好好吃饭怎么办?”这些皇孙自编书事了,被遣回去后,每日除了在百孙院正堂温习《孝经》外再无他事,李德几个年长的倒还好,有家有室,还可以乐舞排遣,只是微微地发了福,几个小的除了吃就是玩,李千里这厮最狠,两三年间从一个修长挺拔的俊俏小郎,活生生养成了一个大胖子,守礼虽不曾像他们那般荒废,可也不能养出坏习惯。
仙仙笑:“小大郎的性子娘子还不知么?可是那憨吃贪玩之人?”
我道:“总是防微杜渐。”走到外间,守礼已随着宫人到了门口,小家伙穿得倒很郑重,以一顶银白嵌珠小冠束发,下穿素白团花锦衣,素缎袴,六合靴,他长大了,脸比先稍圆了一些,肌肤白嫩嫩的,像我,两肩收细、背脊挺拔、走路时轻盈矫健,却像是阿欢,到了我跟前,已不像从前那般憨娇撒慢,只弯下腰去,规规矩矩地道:“姑姑好。”直起身来,两眼中似盛满了两泓春水,嘴角微挑,不必笑已带了三分笑意:“听说姑姑身子不适,昨日就想来问候了,可姑姑不在,只好今日过来——姑姑今日可好些?”
我一见他,便觉块垒疏散,逗他道:“你看姑姑可好了?”
他便站近一步,将我脸上一打量,点了点头:“看着像好啦。”严肃地看向仙仙:“请的哪位御医来看?用的什么药?一日几服?”
仙仙一本正经地道:“请了张、王二御医来看,开的发散之剂,昨日煎了三付,三餐饭后服了,今日还未服药——小大郎还要问什么?”
守礼偏了头一想,道:“没了。”马上又道:“饮食可好么?睡得安稳么?”
仙仙拿眼看我,我道:“你近日书读得如何?可有不解处?叫你学的算盘,打的怎么样了?那石头的实验呢?”
这小家伙这些时候像是和地球引力杠上了,我早将从前那些“石头”“羽毛”的问话忘了,他却自己跑去做了许多实验,石头、木头、铁块、羽毛…举凡宫中能找到之物,他全都试过,连阿欢的首饰也被他拆好几样,珍珠金宝,扔来扔去,也不可惜,我喜他能找到些事做,故意不加引导,只令他自己摸索,也劝阿欢不要管他。
提到那些宝贝试验,守礼便立刻露出兴奋来:“正要和姑姑说呢。”说话间便转头后看,跟他的两个小宦官忙忙上前,将一个大包裹放在地上,守礼亲自展开,将里面的物件取出来给我看:“姑姑你看,这是金丸。”特地给我掂了一掂,表示这东西确是重物无误,其后又将这金丸放在一个极小的托盘中,托盘四面拴着细绳,细绳牵着一张大纸的四角,细看之下,那纸还非一层,却是许多层糊在一起的,守礼举着这小心拼凑的物件四面看了一圈,问我:“姑姑,我可以站到那上面么?”
我点点头,他便站到椅子上,将这物件举得高高的,两手一松,那金丸便摇摇晃晃地落地,我本以为他已研究出什么热气球之类的东西,没想到这东西还是落了地,有些不解地看他,守礼只对我笑:“姑姑再看。”将金丸自那一套物件中取出来,举在差不多的高度,松手,金丸应声落地,在地上弹了几下,滚在一旁。
守礼跳下地:“几张纸、几条绳,几乎没什么重量,却可大大延缓这金丸落地的时间。可见这落地的快与慢,绝不与轻重相关。我试过,应当是与纸张大小有关,纸越大,金丸落地越慢,可我只有这么大的纸,要是有更大的,就可以再试试——说不定可以让金丸飞起来。”
我心中直如惊涛骇浪一般,转头去打量这小郎,见他满面忐忑,似是在求得我的肯定,仙仙几人都未意识到这里的意义,只是笑嘻嘻在旁凑趣:“了不得,小大郎修炼起神仙术了。”
守礼眼巴巴地在看我,我半晌才伸出手,小心翼翼捡起那颗金丸,感觉自己捏着的不是金丸,而是牛顿的苹果:“大郎…怎么想到这个的?”
守礼一面偷看我的脸色,小声道:“最早是用木头、石块和铁块在试,发现只要差不多大小,无论轻重,都是一样落地,可一旦换了纸或羽毛、布帛,便大不一样。倘若将布帛拧成一团,又不一样。我想,大鹏扶摇直上,靠的是绝大的翅膀和风力,则这些物件落或不落,是不是也靠着风力呢?我…我就仿着做了个翅膀,拿羽毛做,拿纸做,试了许多遍…姑姑是对的,这些物件落地时间有短长,不是因重量,而是因风力。纸团成团,落下去就快,张开来,乘风而落,就慢,纸札带了金丸,很重,却可以飘飘而落…我只是不知,室内明明没有风,为何也会如此——姑姑?”
我笑着看他,牵了他的手到一旁坐下:“你没有错,室内是有风的,不过室内的风,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风,是‘空气’,空气也是有力道的。”我以为自己已将前世的知识都忘得差不多了,可真的讲解起来,却发现许多事早已铭心刻骨,不必特地去想,便可脱口而出,“…纸札与空气接触的面积大——面积,便是物体所占的地方的大小,不是所有的地方,是在这一面上这一块的地方…”
我们直讲到了晚上,仙仙提醒了几次,才略用了些饭,饭后守礼还想留在这里,他奶娘反复催促,我又答应明日再教,他方恋恋不舍离开,我在门口看着他上了舆,将离开时又想起什么,叫住他问:“你阿娘…还好么?”
他在舆上微微欠身:“阿娘不舒服,这两日除了问起居外都不曾出门。”停了一停,忽地问我:“姑姑…阿七怎么样了?”
我怔了怔,道:“你阿娘怎么说?”
他看着我:“阿娘说她出宫养病了,但是七郎说她…没了。”
我垂了眼,半晌方道:“李千里那厮的话,你也肯信么?”
守礼露出大大的笑来:“我就知他骗我!以后再也不和他一起去看百戏了。”
作者有话要说:
第343章 社魁
我自母亲的指点中领悟了些灵感, 并不亲自去办拍卖的事, 只将冯永昌叫来, 略与他说了此事,命他“选得力干练之人”前去准备, 若是办得好,以后这事便固定交给他办。
冯永昌自是应承得欢快, 因我叫他荐人, 马上又说出几个名字,倒都是我叫得出名字的家仆,我刚要点头,略想了一想,又道:“此事非是为我, 而是为陛下,办事之人, 在陛下那里也是要挂名的——你明白么?”
这厮别的或许不行,希旨媚上的本领倒是一等一的,立刻便笑道:“小人回去再访一访, 自士人中择出几位——只怕小人人卑位轻,这些人未必肯就听了小人的。”
我斜眼看他:“这些年你上上下下地办事,自州县至台省,何处不至?从未见说因位卑言轻,就有谁轻慢于你了,怎么这回忽地就‘位卑言轻’了?”
冯永昌见我不悦,搓手干笑着不说话, 我看他一眼,又看了一旁立着的冯世良,倒想起他这般的缘由来——冯世良自他残疾后,又另收了一个义子,去岁选进掖庭,已授了七品实职,想是这厮看着眼热——便道:“这事若办得好,我荐你一个六品。”
冯永昌笑得眯了眼,只差没拍胸脯立军令状,我见他模样,少不得又道:“为陛下办事与为我办事不同,为我办事,办错了,不过家法稍事惩戒,为陛下办事,须得忠勤俭省…不许有贪墨、舞弊等事,懂么?”
不知他听未听进去,反正面上总是应着,一路轻飘飘地退出去,脚步轻快,好似残疾都不再了似的。
我看着他的背影,莫名地觉得有些难受,起身在殿中绕了一圈,本想去寻崔明德,信步而出,行到一半,不知怎地却看见百孙院了,母亲已应了我的请求,准武承嗣一日隔一日地去东宫授课,诸皇孙亦随往附学,百孙院白日里便显得冷冷清清,素日还有些丝竹之声,今日却是静悄悄,从外到内,一声不闻。
我轻轻地走近阿欢的院子,到里面才见两个小内侍坐在廊下,边打着呵欠边烤火,其中一个细细碎碎,似是在说什么,另一个显然没在听她的话,敷衍地点着头,到近前才看见我,慌慌张张起身,几乎踢翻了火盆。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