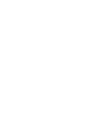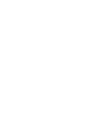全道门都欠我一个人情 - 第121章回春之日
如一知道自己的抗议向来无效, 只得提前做好准备, 将围墙又往上加了一尺,并将贴墙而生的杏树往内挪了几丈。
果然,此招大大克制了封如故。
不管生前死后, 他都是一只如假包换的懒猫,墙太高, 他也懒得爬,只偶尔爬上树,在枝杈上晃荡着腿向外张望, 或是在墙下坐着,望着墙外世界, 不知是向往,还是怀念。
他怀里搂着灰猫, 灰猫轻轻舔他的手指, 而他把灰猫捧起来, 想要礼尚往来一番, 却感觉对方毛多厚实,无从下口,就只在它的额头亲了一口,意思意思。
他在外面和猫玩累了, 就会大大咧咧来到如一正在俯首看书的桌案前,自顾自趴在对面, 酣然入睡。
猫这种动物, 确实是很合封如故的习性。
十年间, 他虽然居于“静水流深”中,但身体抱恙,在“七花印”剧毒作用下,忍受伤疲之苦,整整十年,未曾睡过一个好觉,现今总算一口气补了回来。
仅仅是看他睡在自己面前,如一便能感到由衷的幸福安宁。
这感觉实在很好。
如一翻一页书,便看他一眼,盯着他的时间久了,竟难得犯了孩子气,越过桌面,轻掐一掐他秀气的鼻尖小痣,旋即马上收回手来,作正襟危坐、认真学习状。
封如故感到外界的动作,迷蒙地抬起眼睛,四下环顾,未能寻获罪魁,就继续埋在臂弯间,蹭一蹭脸,把自己蹭得清醒一些后,又把脸枕在小臂上,歪头看着如一。
如一面色沉静,双眼紧盯书页,一副郎心如铁的模样。
封如故对他笑开了:“喵。”
如一倒吸一口凉气,攥书页的手紧了紧。
封如故绕过书桌,手捧着小暖炉,贴着如一的椅子就地坐下,将头枕靠在他腿上,撒娇地拱了拱。
如一握着书,目不斜视,心脏狂跳:“你……义父,起来罢,地上太凉。”
但封如故却像是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似的,盯着他胸口看了半晌,灵活地从他手臂与腿的夹缝间挤进去,坐在他的膝盖上,撩开他僧袍前襟,朝内张望。
如一一把抓住领口,同时压住他的手:“你……”
封如故秉承猫爪子不可被压于下的原则,迅速把手抽出,压在他的手背上,探头探脑道:“你胸口在亮。”
如一捂住胸口:“……”
封如故好奇求知:“为什么啊。”
如一盯着他被自己舌头润湿了一片、薄薄闪着一丝水光的唇畔,揪紧膝上一层衣物,反复告诫自己,佛门清静之地,不可胡来。
且义父心智不全,此刻妄为,实在是有趁人之危之嫌。
他偏过脸来,勉强答道:“因为……贫僧,心里有一个人。”
封如故表示听不懂。
如一放柔了声音同他解释:“他只要叫门,我就会在心里给他点一盏灯笼,欢迎他归家。”
封如故似懂非懂,低头在自己胸口摸索:“我怎么没有?我心里是空荡荡的吗?”
如一心微微一痛,仿佛亲手扯裂了心中创伤:“义父这样……就很好。”
心有挂碍,就有了忧怖。
哪怕封如故接下来的一生,是空茫茫的一片雪原,如果这样能换他无忧无虑,欢喜一世,也不差。
左右这小院僧舍,是按照义父与自己共同拟下的理想家园蓝图建造,义父愿在这里住多久,都遂他所愿。
待来日,他养好魂魄,自己也会带他出去游世。
他已长大了。不是十三岁的、无法保护义父的小红尘了。
……
年尾将至,僧众们没有过年的习俗,但山外人对这一年一度、辞旧迎新的日子,很是看重。
寺中前来敬香之人络绎不绝,为求寺中安全,如一外巡的时间增多了,然而一天之间,他总有八个时辰,是完全属于封如故的。
后来,如一见封如故和小灰猫都对廊下挂着的风铃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就在封如故颈上系了一枚铃铛。
他果然很喜欢铃铛声,常常在半夜醒来时,下床在屋里走来走去,铜丸碰银壳,弄出一室清脆活泼的铃音。
新年第二日,寒山寺间香火愈旺,在南山小院里,已经能日夜不绝地嗅到檀香气。
灰猫逃出去看热闹了,留下懒得爬墙的封如故一个守在家里,靠在廊柱底下,闭眼袖手,烤着红泥抟就的小火炉,在火炉边摆上一圈板栗,静待烤熟入口。
“人柱”被如一留下保护他。
经过一年的人世生涯,“人柱”小五对封如故那曾经浓烈万分的男女之情,已尽数转化为母性。
她自作主张地从如一的衣架上摸来一件僧袍,披在了封如故身上。
封如故睡得很香。
在衣服披上肩时,他缩了缩身体,软声唤道:“……阿爹,阿娘……”
“人柱”绕他飘了一圈,小六俯身抱定了他,满怀感情道:“阿娘在这儿。”
她其他几名兄弟一齐沉默,不想承认自己就这么晋级做了叔伯婶姨。
她的怀抱像是云朵,封如故放松了心神,继续软声讲着自己的心事:“……嬷嬷病了,要请大夫……”
午后时分,天空已见阴晦,封如故的脸在天光下呈现粉白色,缩手缩脚,小孩子似的,叫小六更怀慈母之心。
她正想着该当如何安抚他,就听身后传来“喀”的一声脆响。
一颗板栗被烤得蹦出炉边,骨碌碌在地上打了几转,被烤裂的壳内露出了内里鲜黄灼热的果肉。
封如故睁开眼,看清眼前人的容貌,恍然如梦,一头扎进了她的怀里。
小六:“……?”
然而,片刻之后,正欲撒娇的封如故及时收势,重新抬头,打量她一番,缓缓往后挪去。
他小声嘟囔:“看错了,不是你啊……”
猫的习性,封如故这十年学了个十足十,如今学来,也是驾轻就熟。
他懒洋洋伸了个腰,从地上捡起滚走的栗子,留给自己,并拣了炉上另外七八个烤好的栗子,塞到了“人柱”手里。
……丑东西看多了,也不那么丑了。
立在廊下,封如故突然感觉脸上有细细的颗粒感。
他抬手摸了一下脸颊,仰头观天,神情困惑,不解这是何物。
现今的“人柱”,要比神智模糊的封如故更加见多识广。
她说:“下雪了。”
寒山寺冬日素来少雪,封如故去岁被如一带回寒山寺时,冬日里没有下过一场雪,只是单纯地冷着,而那时,封如故对外界的感知很是迟钝,正热衷于扮演出墙的红杏,还着实让如一头疼了几日。
今年,这场大雪落得可谓声势浩荡,整整一日的鹅毛雪,下得天地都静了。
素雪纷纷鹤委,清风飙飙入袖。
寒山寺旁不远的河流上泊着一只乌篷渡船,船上覆上了一层雪顶,船夫打起一面青旗,示意停工,不再摆渡,自己则提一钓竿,兀自行那“独钓寒江雪”的乐事。
山间积雪难行,来敬香的人稍少了些,如一也腾出了些时间,好回来照料他的猫义父。
屋外落雪愈重,封如故便愈困。
房中的火炉日夜烧得兴旺,银炭静静地发着燃烧的“丝丝”细响。
封如故枕在如一腿上酣睡,小灰猫则抱趴在封如故的臂弯上,效仿了他的睡姿。
如一有些腿麻,但他什么都没有说,甚至没有挪动一下,只是拿手指卷了封如故一缕散开的头发,在指尖缠绕转动,把好好一撮鬓发卷成了小卷毛。
不知何时,封如故悠悠醒转过来,眼望着外面漫天碎琼乱玉,突然清楚地开口道:“我想看石榴花。”
如一放下书卷:“现在还不是开石榴花的时节。”
封如故:“那我要看红杏。”
如一无奈:“……义父。那些都是春天才有的。”
“春天……”封如故喃喃道,“爹亲跟我讲,说来年春天,带我去山上看杏花,看石榴花。”
封如故扯住如一的腰带,把脸埋在了他的小腹位置,闷声闷气地问:“……春天什么时候会来啊。”
如一张了张嘴,正欲作答,突然住了声。
他把封如故的脸摆正,叫他面对自己,并把额头轻轻贴上他的额心,依恋地蹭了蹭:“……马上就来。”
寒山寺中,有青衣小僧在菩萨殿前扫雪。
天气寒冷,呵气成冰,小僧人把竹笤帚放下,把手拢在唇边呵气时,眼角瞥向南山,一时瞠目。
他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忙揉一揉眼睛,定睛再望——
南山一侧的积雪迅速融化,有半副阴晦天云被挪去旁处,原本融融的冰雪尽数融化,化入泥土。
在地下沉睡的百虫感受到土地的湿润暖意,纷纷冒头,各自疑惑,此次冬眠为何如此之短。
花木迅速吐蕊抽枝,起初是林空色暝、春浅香寒,很快,绿杨成影,红杏倚云,榴火似的春色流遍全山。
寒山寺方丈特遣人来问,如一为何强行运功、做出如此大的虚耗,也要提早还春?
“落雪无趣。”如一倚门道,“我提早迎春,有何不可?”
来询问的小僧人无言以对,讪讪离去。
如一重新关闭院门,一抬头,又看到坐在丛丛红杏枝头,蠢蠢欲动、妄图出墙的一枝小红杏。
他无奈一笑,纵身上树,拦腰抱住他的腰身,单足翩然落地,洒下一院银铃脆响。
寒山寺春色早到,被姑苏城内百姓视作神迹一事,自不必提。
在距离寒山寺与风陵皆有千里之遥的一处小城酒肆中,一名身着白衣的俊美道人踏雪而入,肩上背着两把剑,一柄螺青色,一柄纨素色。
在柜台后打盹的小二听到门帘响动,急忙抹去口水,起身相迎,殷勤招待:“道长,要喝点什么酒?”
常伯宁客客气气:“劳驾,一壶黄酒。”
“得嘞。”小二擦了擦手,“道长,年节了,这是要回哪位仙府?”
“何来仙府?无名之地罢了。”常伯宁呵出一口冷气,“有事在外,今年也不回去了。”
小二及时捧上一壶温好的酒,常伯宁道一声谢,斟出半杯儿来,一饮而尽。
小二见他饮酒速度太猛,不是酒中老饕,便是错估了自己酒量的愣头青,忍不住提醒:“小店酒烈,道长饮得慢些。”
常伯宁温和道:“无妨。我酒量很好。”
小二好奇:“天生的?”
常伯宁淡道:“总能练出来的。”
他放下酒杯,又置下一块碎银,并取出一只精致的银链酒壶:“这酒很好。再替我打上一壶吧,我带走。”
小二眼睛放光,忙接过碎银,搁在口里咬上一下,喜笑颜开地拿起酒壶:“马上来,马上来。”
小二不敢擅自收下这么大额的银两,去后院敲老板娘的房门了。
常伯宁正要举杯,眼睛余光瞥向帘外的冰雪世界,神情骤然一凝,搁下酒杯,飞身掠出,不由分说,一把擒住了帘外过路之人的衣襟,反手持“今朝”剑鞘,当胸一击,险些击碎他的内丹!
长街之上,风雪漫漫,路上并没有别的行人,路旁的店铺也关了个七七八八,是而无人注意到长街上这一瞬的骚动。
常伯宁将他摁倒在地。
粗糙雪粒簌簌扑在他的脸上,让他的声音和面容一道变得模糊起来。
“给你一次机会。”常伯宁声音很软,他的修养如此,说不出太激烈的言辞,在这种情况下,仍显得过分温吞,“回答我,龙山门金门主之子金映生,你在酒旗镇炼尸,吸取生人活气,为己修炼一事,是你与魔道行尸宗勾结做下的?”
“常……”来人受此突袭,惊慌却早盖过了疼痛,“写信约我来此地的人,是你?”
常伯宁只问一件事:“你以为是谁?”
“我还以为……”慑于常伯宁威势,金映生双目一闭,低声招供,“我还以为,是……是那个人,是那个使唐刀的人……他杀了道门人,背着尸身,堂而皇之经过我龙山门,恰好与我相遇,我本要擒捉他,他却说……说,要我按照他的要求,帮他在龙山门藏经阁上摆放尸体,否则将来,龙山门之秘难保,他手里还握有我与行尸宗来往的信件证据,所以,我……”
常伯宁拿“今朝”剑鞘抵在他胸前,急问:“你还记得那人面容吗?”
金映生为求保命,自是言无不尽:“记得记得!我可以绘给——”
话音未落,常伯宁持握剑鞘的手,竟受了一道无来由的重击,往前狠狠捅去!
金映生胸口,竟被剑鞘捅了个对穿!
金映生噗的一口热血吐出,将他面前三尺白雪尽皆染透!
常伯宁骇然回首,但见一道红衣身影,静立在酒肆飘扬的旗帜边,衣袂被白雪卷起,指尖仍泛着一道未散流光,面容难辨。
常伯宁猛地起身,却突觉头晕目眩,扶剑没入积雪,才堪堪稳住身子。
他低声道:“你——给我……”
这些日子来,他唯一入口的,就是方才的一杯黄酒。
那人不答,飞身落于长街之上,眉间肩上白雪皑皑,也不知在屋上站立了多久。
常伯宁脸色苍白,竭力想逼出体内余毒,却手脚麻痹,力不能支,向侧边软倒下去。
那人跨前一步,将昏迷的常伯宁单臂接住。
常伯宁软在他肩侧,呼吸深深浅浅地在韩兢耳边浮动。
……即使昏倒了,也仍是心不静。
“你现在已经聪明一些了。”韩兢低声对他说,“只是莫要养成这饮酒的习惯。我给你一个教训,今日之后,便尽快戒了吧。”
他将没入金映生胸口的剑鞘拔出,在积雪上甩出一道新鲜血线,无视了金映生死不瞑目的面容,平静地对常伯宁说教:“三日未睡,连日奔碌,总是不好的。”
言罢,韩兢将常伯宁拦腰抱起,背起他的剑,迈步向长街尽头走去,轻声道:“……抱歉,打断了你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这个人,我先替道门处理掉。等你休息好了,再设法找到我吧。”
风雪在地上的尸身上披了一层浅浅白色。
待小二拿着酒壶赶出门来、左右张望时,过大的风雪,让他把倒卧着的人当成了一堆被运货人弃置在此的破麻袋。
雪草草掩埋了血迹,只剩下韩兢留下的一道浅浅足迹,蜿蜒行向了远方。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