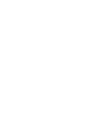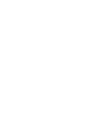美国8大名案 - 第6章
联邦毒品局始终不承认尤金尼奥·契亚尼尼之死与他的线人身份有关。据他们掌握的情报,契亚尼尼从意大利偷运出的10公斤海洛因到达美国后,因分赃不均而导致了同伙间的争斗,契亚尼尼于是派他的妻弟悄悄去意大利,又带回了6公斤海洛因。他的妻弟在契亚尼尼遇刺前一个月被捕。所以毒品局认定契亚尼尼死于贩毒团伙之间的内讧。
笔者后来知道,以上的一大段便是出自瓦拉奇备忘录,亦称瓦拉奇档案,或瓦拉奇文件。
何为瓦拉奇备忘录?简单地说,就是关于约瑟夫·瓦拉奇黑手党生涯的综合资料,包括联邦调查局和联邦毒品局的审讯记录、瓦拉奇本人的交代和在参议院作证时的证词,以及后来在美国司法部的敦促下撰写的回忆录。
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罗勃特·肯尼迪对瓦拉奇备忘录的评价是,这“是美利坚合众国在与国内黑社会恶势力的战斗中最重大的情报突破”。
在瓦拉奇备忘录之前,执法机关看到的是一个个孤立的,表面上互不相干,却又层出不穷的谋杀案、绑架案、失踪案、毒品案、纵火案、爆炸案……瓦拉奇备忘录将所有这些零星案件,连同它们的作案人和幕后操纵者一起,摆放在了一张巨大的,精心编织的恶势力网络图上。
在瓦拉奇备忘录之前,举一个例子,联邦调查局纽约地区的办公大楼里,“黑帮处”只有四名工作人员和一间办公室,而“共产党处”却有400多人,占据了整整一个楼层。瓦拉奇备忘录之后,“黑帮处”人数激增,并在60年代末跃升为那里最庞大的部门之一。
瓦拉奇备忘录问世后十年左右,70年代初期,在美利坚大地上生殖繁衍了70余年的意大利黑手党,或“科沙·诺斯卓”土崩瓦解。尽管纽约五大家族和其他地区的一些残部或散兵游勇仍在继续负隅顽抗,但曾盘踞于各大都市中的0多个家族从此不复存在。
耐人寻味的是,瓦拉奇备忘录并非这位黑手党“老兵”——0余年来,约瑟夫·瓦拉奇在“科沙·诺斯卓”中的级别一直没有超过“兵士”——经过深思熟虑、精心策划的结果。事情的起因纯属偶然,皆因其当事人犯下了一个在正常状况下不可能犯的错误。
196年6月日早晨7点半,正是亚特兰大联邦监狱早饭后放风的时间。最近,监狱里的几座房子需要维修,工人们把拆下来的垃圾废料等物堆放在操场的角落。狱方并不是特别在意那些可能被用作武器的砖瓦棍棒,因为这座监狱里关押的都是非暴力犯人。
忽然,第8811号囚犯,因涉嫌贩毒而被收监的57岁的约瑟夫·瓦拉奇从地上操起一根两英尺来长的铁管,朝一位背对着他的犯人冲过去。只眨眼的工夫,那人便血流如注,颓然倒地。
瓦拉奇马上被带进了禁闭室,俗称“蹲小号”。当沉重的铁门在他身后砰然关闭后,他居然由衷地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安全,接着就觉得自己饥肠辘辘。他已经好几天不敢吃东西了,总害怕有人会在他的饭菜里下毒。
瓦拉奇的好心情很快便荡然无存。看守过来告诉他,医生说,那个被他用铁管撂倒的约翰·约瑟夫·绍普生命垂危。
瓦拉奇倒并不在乎那个人是不是生命垂危。但是,“约翰·约瑟夫·绍普?”瓦拉奇一下子懵了,他记得他那一杠子明明是砸在了约瑟夫·狄坡勒摩的头上。
在此之前几个星期,瓦拉奇已经预感到了将有大祸临头。另一名和瓦拉奇因同一案子被捕的囚犯指控他向联邦毒品局告密。也就不过一夜之间,瓦拉奇发现他成了他自己曾成功地实施多次的黑手党暗杀计划的目标。
瓦拉奇的一生中先后1次被捕,为了换取较轻的惩罚,他确曾向有关当局通报过一些毒品走私方面的消息,但和死在他手中的尤金尼奥·契亚尼尼一样,瓦拉奇从来没敢透露过半点有关“科沙·诺斯卓”的情报。
进入6月以来,瓦拉奇已侥幸逃脱了三次险些让他丧命的袭击。第一次是有人给他送放了毒的食物。第二次是一帮狱中的黑手党分子把他赤身裸体地堵在了澡堂子的角落。第三次是故意让他卷入到一场殴斗之中,再趁乱朝他捅刀子。
当时,“老头子”维克多·靳诺万斯也在这里。50年代初期,因查理·露其亚诺返美无望,老头子便遂心如愿地登上了老板的宝座。按规定,他们的家族应更名为靳诺万斯,但人们背地里还是称露其亚诺家族。1959年4月,维克多·靳诺万斯因“策划贩毒阴谋罪”被捕,判刑15年。
约瑟夫·瓦拉奇是在196年月来到亚特兰大联邦监狱的,老头子不仅盛情邀请他搬入他的房间——那间8个人的牢房里只住了5个人——而且亲自出面找看守通融。多年前,维克多还做过瓦拉奇婚礼上的男傧相。就在那场殴斗后几天,据瓦拉奇备忘录所述:
一天晚上在我们的牢房里,维克多开始对我说什么,你到市场上去买了一筐苹果,里面有一个烂的,你怎么办呢?当然要把烂苹果拿掉,不然到后来整筐苹果都会烂掉。
我一直想打断他的话,但他摆摆手要我住口。我实在忍不住了,说:“如果我真是做错了什么你就明说,然后给我一粒药丸,”指氰化钾,“我当你的面马上吞下去。”
他说:“谁说你做错什么了?”
我没话可说。
他又说,我们是多年的老交情了,我要送你一个吻,为了我们过去在一起的那些好日子。
我心说,ok,我也送你一个吻,就回吻了他。
他问我:“你有几个孙子?”
我说:“三个。你呢?”我记得他说六个,我说:“你挺有福的。”我的意思是让他知道,如果他对我的孙子感兴趣,我也会对他的孙子感兴趣。
我上床睡觉,听见邻床的绕夫·瓦格纳轻轻地嘟囔了一句:“死亡之吻。”我明白他是在警告我。我躺在床上装作没听见。可是,谁睡得着呵?
我不相信什么“死亡之吻”的鬼话,但是我知道,每次要“做”掉某人之前,就会对那个人特别友好,这样他就不会防备。按老早的习惯,当你见到另一位成员时要相互在脸上亲一下。后来查理·露其亚诺当了老板就改成了握手。“但是,”查理说,“在外面,比如餐馆里见了面,还是要打kiss的。”
6月16日,约瑟夫·瓦拉奇走出了自卫的最后一步,他要求看守把他关进禁闭室里。问其理由,瓦拉奇说:“有人要杀了我,或者被我杀掉。这个理由够充分吧?”瓦拉奇在禁闭室里指名道姓要见联邦毒品局的乔治·伽弗尼,此人原为毒品局纽约办公室的负责人,现任毒品局总部执行主任,是与瓦拉奇打过交道的最大的政府官员。瓦拉奇带给他的口信是:“我打算都告诉你。”
然而,远在纽约的乔治·伽弗尼却迟迟没有回音,瓦拉奇又不愿意“告诉”监狱里的官员们,“你们不懂。”他对他们说。后来,在瓦拉奇备忘录里,他承认他当时并没有真正打算交代什么,只是想再和乔治·伽弗尼做一笔交易,用几条情报买一张去别的监狱的路条。几天后,瓦拉奇被送回了和老头子同住的牢房。
瓦拉奇只能背水一战了。他已经作好了死的准备,只是琢磨着如何拉上几个垫背的。他在心里圈定的第一个名字就是约瑟夫·狄坡勒摩。6月初的一天,一向和他没有什么交往的狄坡勒摩突然递给他一份很不错的牛肉三明治,说是从厨房为老头子开的小灶里偷出来的。瓦拉奇没有接,因为他觉得蹊跷,也因为他从来就讨厌这个成天鞍前马后围着老头子瞎转悠的小喽Α9然,瓦拉奇后来发现约瑟夫·狄坡勒摩悄悄地把三明治扔进了垃圾桶里。
瓦拉奇不打算干掉老头子,他觉得这样太便宜他了。他知道老头子在家族内部的种种劣迹,特别在查理·露其亚诺远走拿玻里后。维克多做掉过不知多少与自己不和的下属,尔后又栽赃他们是警方的线人。瓦拉奇知道不少家族成员都对老头子恨得咬牙切齿,也知道若要在“科沙·诺斯卓”内部处置一位老板级的人物是必须经过审判的。瓦拉奇相信迟早会有这样一个对维克多·靳诺万斯进行公开清算的机会。
然后就到了6月日早上。自打从“小号”里出来后,瓦拉奇只能以他能搞到手的寥寥几只食品罐头充饥。厨房里有黑手党囚犯,他刚来时就听说了。他们不仅敢在看守的眼皮子底下给老头子开小灶,也敢明目张胆地往饭盒里搁砒霜。瓦拉奇甚至不敢去洗澡,连上厕所也是小心翼翼左顾右盼。又是差不多一宿没合眼,瓦拉奇觉得头重脚轻,走起路来就像一个机器人,因为饥饿,因为没睡觉,更因为紧张。他尽可能远离人群,但又不敢靠角落太近。就在他神经兮兮的时候,据瓦拉奇备忘录的叙述:
我忽然看见三个人正盯着我交头接耳,他们离我大约50码,然后开始向我这边走来。
我慢慢地后退,一边看了看身后。那堆垃圾旁边的地上有一根铁管。我弯腰去捡铁管,听见有人在离我很近的地方说:“哈罗,约瑟夫。”我抬眼看时,那人已经转过身,好像正在和那三个人打什么手势。他的背影太像约瑟夫·狄坡勒摩了。
…………
典狱长在禁闭室门上的小窗口亮出一张照片,问:“你认识他吗?”我说:“不。”他说:“是吗?他就是你打伤的人。”
我一下子堕进了云雾山中。
两天后,那个被瓦拉奇误伤的名叫约翰·约瑟夫·绍普的倒霉蛋死在了医院里。他犯的是盗窃邮件和伪造文件罪,与黑手党全无关系。
联邦调查局特派员詹姆斯·福林后来认为,这起“误杀事件”促成了瓦拉奇一生的转折。“瓦拉奇对他所做过的事情从来没有后悔过,只除了这一次。他绝对不能原谅自己错杀了一个不相干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他多年的信念、意志,可能还有自尊和自信。倘若那天他杀掉的确实是一个企图袭击他的黑手党人,就像他真正打算做的那样,恐怕就不会有后来的瓦拉奇备忘录了。”在联邦调查局负责审讯的官员中,詹姆斯·福林和瓦拉奇相处的时间最长,他深得瓦拉奇的信任,成了他无话不说的“知己”。
瓦拉奇终于离开了亚特兰大联邦监狱。在等待约翰·绍普凶杀案审判的同时,他通过法庭为他指定的律师们再次与纽约方面联系。7月17日,亚特兰大法庭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瓦拉奇终身监禁。同日,联邦毒品局出面将他秘密递解回纽约,用“约瑟夫·迪马可”的化名关押在西彻斯特地区监狱的隔离区。
约瑟夫·瓦拉奇是铁了心要和“科沙·诺斯卓”作对了。其实在他的心目中,那个庞大的黑社会组织已经被具体化为“老头子”维克多·靳诺万斯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仇人。在他的言谈中常常可以听到诸如此类的话:“我反正已经活腻了。但凡我在这个世界上多混一天,就要给维克多那个老小子多添一分堵。”或者,“我这可不是在出卖谁,是维克多不仁不义,是他先背叛了我。”或者,“你不是一直都对那些老板们不服气吗?现在你就可以毁了他们。”很明显,瓦拉奇“决定与联邦政府合作”的真正目的,是要报复他原先的主子们。
但他有的时候又很消极悲观:“我是什么人?一个小兵卒子。谁会听我的?谁会相信我?”“我坐在这里跟你们讲这些有什么用?‘科沙·诺斯卓’太庞大了,它的地盘远远超出了美国,它整个就是一个‘第二政府’。”
不管怎么说,在瓦拉奇不间断地喷云吐雾的过程中——在被提审期间,他每天要抽掉包骆驼牌香烟——联邦毒品局从瓦拉奇嘴里获得了比他们所预料的多得多的情报。一旦审讯和交代的内容超出了毒品走私的范围,早有风闻的联邦调查局便迫不及待地插手进来。到196年9月底,瓦拉奇已经被完完全全地置于联邦调查局的“监护”之下。詹姆斯·福林和他的同事们每周四次到西彻斯特监狱提审瓦拉奇,每次三至四个小时。
与瓦拉奇打过交道的官员们都说,瓦拉奇有着惊人的、摄像机般的记忆力,他对许许多多往事的印象堪称“记忆犹新”,他在述说过程中几乎从未弄错过诸如姓名、时间、地点、前因后果等等细节。根据瓦拉奇备忘录所提供的第一手——瓦拉奇本人亲历的——和第二手——“那小子告诉我的”——材料,联邦调查局和纽约警署先后澄清了几十件悬置多年的冷案。
联邦调查局对瓦拉奇的审讯调查持续了将近一年。这期间,瓦拉奇“叛变”的消息传到了“科沙·诺斯卓”内部,几个家族为瓦拉奇的人头联合标出10万美元的价格。追究起来,皆因联邦调查局对瓦拉奇的案子一手遮天,联邦毒品局惟恐他们的功绩被无端抹杀,于是故意透出口风,着意强调是他们发现了瓦拉奇这颗重磅炸弹。不久,黑手党得知瓦拉奇已经被转移到了纽约,但他们以为他是在曼哈顿的某一个旅馆里,于是派出大批人马在那一带搜寻数月。
经美国司法部批准,联邦调查局决定将计就计,让约瑟夫·瓦拉奇到国会公开作证。按照最高法院院长罗勃特·肯尼迪的要求,国会专门成立了以参议员约翰·麦克列兰为主席的“集团犯罪及毒品走私调查委员会”,也叫“麦克列兰委员会”。
196年9月9日,约瑟夫·迈可·瓦拉奇由军事警察押送,乘专用直升机到达华盛顿特区监狱。第二天,便穿戴一新地出现在那座古老的参议院办公大楼里。瓦拉奇坐在证人席上,他的面前,是衣冠楚楚正襟危坐的政治家们,和对准他目不转睛的电视摄像镜头。日复一日,瓦拉奇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他的骆驼牌香烟,他的故事,也裹在那浓浓的烟雾里,一段接一段地从他的两唇之间源源不断地流出。那些听似平淡、甚至麻木的语言,一层层地揭去了黑手党的神秘面纱,一件件地抖落出了他们黑暗而肮脏的秘密。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民众从一个亲口承认涉嫌起谋杀案的黑手党人嘴里听到了“科沙·诺斯卓”,听到了家族和老板,听到了血誓和合同,还有那些他们以前也略知一二的刺杀、绑架、毒品走私、收买警方、贿赂官员等等真相。
瓦拉奇详尽地讲述了“科沙·诺斯卓”的内部结构、等级制度、操作规程及行动方式,讲述了纽约的五大家族,和与之仅一江之隔的新泽西州诺瓦克家族,讲述了作为“科沙·诺斯卓”支柱产业的贩毒、赌博、彩券交易、高利贷、劳工工会以及在禁酒令废除之前的黑酒生意,并就警方名单上8个黑道人物中的89人提供了较为具体的情报。
这里有一些例子。譬如高利贷,任何不能通过合法途径获得贷款的人,都可以找“科沙·诺斯卓”借钱,利率一般是每周1%。许多人由此而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他们被迫不断地借钱仅仅是为了偿还利息。等到濒临破产时,他们的房屋、产业、生意等便名正言顺地转到了“科沙·诺斯卓”手里。原纽约市水电委员会的简蒙·马可斯,便是因为借了年息105%的巨债而最终沦为了“科沙·诺斯卓”的“上层走狗”。高利贷带给“科沙·诺斯卓”的年收入是以几十亿美元计算的。
关于“科沙·诺斯卓”如何操纵劳工工会,也有一个例子。纽约五大家族之一的老板弗兰克·科斯蒂罗每天去曼哈顿一家宾馆洗桑拿。某日,值班经理对他说,客人们见到他都很紧张,请他能不能不要经常光顾。第二天,该宾馆的女佣、招待、清洁工、电梯工、厨师等等全员罢工。几小时后,总经理亲自打电话,不仅毕恭毕敬地请弗兰克·科斯蒂罗回来洗桑拿,还给他免费优待。
约瑟夫·瓦拉奇在回答参议员们的提问时说:“怎么说呢,当一个人习惯了这些被你们称为欺行霸市、敲诈勒索、杀人越货的勾当后,他就不觉得他是在犯罪了。譬如我,我有一些吃角子机器,我从来不认为那是违法的,因为大家都有。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跟你讲清楚。我有夜总会、服装厂还有几匹赛马。人人都在倒彩票……得,我要怎样说你才能明白呢,参议员先生?”
另一位参议员埃德蒙·摩斯基问,“科沙·诺斯卓”和黑手党是否同一团体?
瓦拉奇答曰:“参议员先生,在我待在里面的0多年里,没有人管它叫黑手党。”“黑手党,那是外人的叫法。”
这里应该略为解释一下。据史料记载,19世纪末叶,美国出现的第一个意大利黑社会组织确实叫“黑手党”,其名源于该组织寄出的恐吓信中,落款处总画有一只狰狞的黑手。当时的纽约警署颇下了一番功夫,才于1910年将“黑手党”肃清,但其名称却在美国民众中一直沿用至今。所以如果不需要特别的精确,按一般人的常识,“黑手党”和意大利黑帮是同义词,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或者说主要指的就是“科沙·诺斯卓”。
听证会上也有一些让瓦拉奇摸不着头脑的问题。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卡尔·柯梯斯想了解黑手党在该州的情况,那是中西部一个比较偏远的州。柯梯斯参议员的问话中提到了那里最大的城市俄马哈。瓦拉奇想了想,又和身边的司法部官员耳语了几句。电视机前的观众以为,参议员提出的一定是一个十分关键、需要慎重回答的问题。谁知瓦拉奇对着麦克风说出的话却是:“这个俄马哈到底在什么鬼地方?”
1964年6月底,鉴于瓦拉奇证词的重要性,司法部要求他以回忆录的方式将自己的亲身经历书写成文,以免遗漏掉在审讯和作证的过程中可能被忽略的细节。瓦拉奇只有七年级的文化水平,一位华盛顿地区的报纸编辑自愿担当了他的助手。此后的1个月里,瓦拉奇磨坏了几十支圆珠笔,在司法部提供的稿纸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了0多万字,共计1180页。当他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瓦拉奇对他的“助理编辑”说:“我觉得我的写作能力比刚开始时更棒了,你说呢?”(未完待续)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