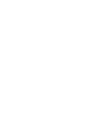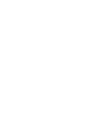人人都爱本教主 - 分卷阅读10
再问:“你白天看得到烟花么?”
我默了许久:“_……看不到。”
江策问:“你如今还有几个烟火令?”
我道:“一个!”
江策道:“很好。”
我松了一口气,幸好季清之给了我三个,到晚上我再去放一放。
吃过蛤蟆,我满足地睡了过去,到傍晚时分,我又出去找了一些吃食填饱肚子,待天色彻底暗下来后,准备出去放烟火令求援助。
我摸了摸内衫,摸了摸裤子,再翻了翻山洞,本座的烟火令不见了!
我问江策:“你看到我的烟火令了么?”
江策道:“你不是收在怀里了么?”
我道:“是啊!可是他不见了!”
江策十分淡定道:“你连暴雨梨花针都能丢,再丢个烟火令也不足为奇了。”
本座十分羞愧,跑出去一阵乱找,将今日走过的地方都找了一遍,可惜还是不见烟火令的踪影,我回去苦着脸道:“我的烟火令找不到了。”
江策道:“既然找不到,那就随遇而安罢。”
我心里十分忧伤,虽然江策在这慢慢疗伤十分安全,但我的寒毒两日后就要发作了!江策伤得如此重,根本无力助我度过难关,难不成我注定要命丧于此?本座连坠落悬崖都死不了,难不成要死在这小小的寒毒下!
入夜后的山间十分寒冷,我中午将外衫烧了烤蛤蟆吃,如今点了一个火堆还是觉得冷飕飕的。
江策见我还翻来覆去,道:“你怎么还不睡?”
我道:“有些冷。”
江策道:“我也觉得有些冷,你过来我们一起睡。”
我心中一想,觉得十分有道理,便凑过去跟他一块睡了。两人搂在一块的确暖和了许多,过不了多时我便睡了过去,梦中我让一只吊睛白额大虫袭击了,他用四只大爪抓住本座,对着本座的脸一通乱舔,随后就擒住本座的嘴不放了。
早晨醒来时,本座吓出一身冷汗!
所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虽然我心里万般不敢,但寒毒发作的日子还是如期而至,我握着江策的手,抓紧时间留遗言。
“倘若我这次熬不过去,你也不必伤心,养好伤就离开这里,往后好好保重自己,找个好姑娘就娶了,不要在我身上死磕。”
江策望着我,一言不发。
我望着他的眼神,有些心寒,心说就算你愿意用《采莲心经》挨过寒毒我也是不肯的,可你连提都不提,连虚与委蛇都不愿作上一番,实在太令我心寒!
我以德报怨地出去帮他摘了好多果子,还有备了好几日的饮水,这才悄悄地走了,不带走一片风雨。
当晚,明月高挂,圆如月盘,我坐在离山洞十分远的一块空地上等死。大约从亥时起,寒毒开始发作,从心口往四肢百骸蔓延,来势汹汹,过不了多时就遍走周身,恍若坠入西北苦寒之地,冰冷寒极。
我倒在地上痛不堪言,面前忽然出现一双黑色的靴子,我抬头一瞧,江策站在我面前一动不动地望着我。
我想对他说句话,奈何完全开不了口。
江策忽然蹲下身用单臂将我从地上扶起,一股纯阳之力就如同热流一般徐徐送入我体内。
江策身负重伤,内力受损,靠着一股些微的内力想要逐走我体内的寒毒,根本如同蚍蜉撼树、螳臂挡车!
我身受寒冰折磨,心中又十分不忍,强提起一口气道:“阿策,你快走……你不要管我……”
江策不管不顾,一个劲地往我体内灌入内力。
我见他一副跟我死磕到底的架势,便也作罢,倘若我们今日不能挨过这劫,亦是命中注定,既然不能同生,同死也是了不得的!
随着时间推移,输入我体内的内力越来越弱,最后几乎湮灭不见,江策倒在了我身上,一双黯然的眼撞入我眼底,他筋疲力尽地伸出手搂着我叫道:“阿萧……”
我费劲地伸出自己的手握住他的手,罢了,此生能得这样一个生死相随之人,我已死而无憾!
我的神智开始模糊,恍惚中嘴里流入一股腥热的血流,将这股凶险恶毒的寒毒压制了下去,迷迷糊糊中便昏睡了过去。
25
25、第二十五章 抓奸在床
我再醒来时,已是翌日天明。
我躺在山洞中,瞪着眼前这个根本不会出现的人裴逍。
我道:“你为何会在这?”
裴逍道:“属下收到教主的烟火令就赶来了。”
如此说来,昨日在关键时刻助我度过寒毒的就是他了,我稍稍动了动,这才发现自己枕在他腿上,身上还盖着他的衣裳。
想起昨日的情形,我连忙起身寻找江策,发现他正躺在山洞另一头,这才松了一口气。我跑过去探了探他的鼻息,还好,没死!我道:“他怎样了?”
裴逍道:“属下不知。”
我心说你救本座的时候难道就不知道帮他看一看嘛?真是难为你还记得把他拖回来了!(t_s)
裴逍道:“教主身子虚弱,还请尽快上崖调养。”
我道:“一切等江盟主醒了再说。”
约莫过了两个时辰,江策这才醒了,我欣喜地望着他道:“你感觉如何?”
江策扯了扯嘴角道:“还好,你呢?”说罢,伸出手握住了我。
我怔了一下,总觉得我俩之中颇有种劫后余生,生死相许的味道。正是含情脉脉中,谁知江策一见着裴逍,登时就变了脸色,责问道:“他为何会在这?”
我冷汗津津道:“我放了烟火令,他就赶来了。”
江策道:“你的烟火令不是昨日放的?难不成他天赋异灵,能在白天看到你的烟火令?”
我道:“其实我前几日就放过一次了,你为了救我内力受损,我怎么能再忍心你助我度过寒毒?”
我的原意是:“你瞧本座多心疼你,舍不得你受一点苦,本座不是为了《采莲心经》接近你的,你明不明白明不明白!”
不知为何,听到江策耳朵就变了味。
他道:“萧教主令旨英明,算无遗策,江某自愧不如,既然江某对萧教主已经毫无价值了,那还请萧教主赶紧随着你这位裴右使回去,省得跟着江某受苦。”
呃……这是闹别扭了!
一边是对本座痴心不悔的裴逍,一边是对本座舍命相救的江策,这可真叫本座难办!
虽然裴逍对我情深不悔,可我总觉得他性子太闷,我若是跟他在一起,早晚要闷死。至于江策……他数次的舍命相救,令我铭感五内,恨不得以身相许,这个老情人的可持续发展性还是可以有的!
我一把握住江策的手道:“你这是说甚么胡话!我们数次生死共度你都忘了?你跟我说甚么既不能同生,那就同死这话难道是唬我的不成?你一离开危险就准备不理我了?”
“你……”他望了我一会,叹道:“我如今身受重伤,你跟着我也是受苦,你若是想回去,就赶紧跟你这位裴右使走。若是要留下来,我也不会赶你。”
我道:“我自然是要留下来了,你身子尚未复原,我们在这多住几日是桩好事。”
我金口一开,季清之就开始从山上丢被褥、衣裳、食物等下来,我们将山洞重新收拾一番,条件自然就不一样了。
裴逍身手了得,我也不用辛辛苦苦地逮蛤蟆吃了,想吃烤鸡就是烤鸡,烤兔子就是烤兔子,简直就是饭来张口,衣来张手。
夜里,我跟江策一人卷着一条铺盖睡觉,裴逍坐在洞口守夜。不知为何到了第二日,我的铺盖飞了,居然跟江策卷到一块去了。
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是江盟主从中捣鬼的!因为本座的睡相不曾那么差过!
我窃声问裴逍:“你昨夜可有瞧见对本座不轨?”
裴逍默了一会,道:“教主多虑……”
不对,一定是你看走眼了!本座前几夜就觉得江盟主趁着本座睡着对本座不轨了!本座一定会找到证据的!
江策的伤在洞里修养了五日,刚有些好转便坐不住了,说甚么福州杜家的事不能再拖。我见这黑玉断续膏的药效不错,短短几日就将他手上的伤给治愈了,便也不再阻拦。
我们三人让季清之从崖底给拉了上去,季清之一见我就痛哭流涕道:“教主,属下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呸呸呸,季左使!你在说甚么胡话!”我一脸不悦地望着他。
季清之连忙改口道:“属下口不择言,还请教主恕罪!”
江策道:“我要赶去福州杜家,你是要跟他们一起回正义教,还是跟我一道去?”
我道:“自然是要跟你一道去。”
江策闻言,淡淡一笑。
我让他这一笑,笑得是心花怒放!江策的相貌虽不及李玉林,但其人清光奕奕、英华隐隐、实在是天赐的君子,他这一笑就如同千树万树梨花开,我整个人都沉浸在本座老情人终于对本座笑了的喜悦中。
我想起他身受重伤,连忙换上一副谄媚的脸向季清之道:“清之呐,你上回往本座兜里塞的东西委实是好东西,救了本座与江盟主的性命,你还有没有其他宝贝也一同给本座。”
季清之立马掏出一个大包裹道:“属下早给教主备下了。”说罢,往我怀里一通塞。
我乐了:“多塞点多塞点!”
临行时,我还不忘拉着裴逍悄悄叮嘱了一句:“此行生死未卜,你藏在暗处保护本座与江盟主。”
裴逍道:“属下遵命。”
之后,我与江策两人一骑朝福州而去,他的手才复原,我不忍他的动手,于是一直由我驾马。
江策调侃道:“你这回可别走错路了。”
我道:“_……我保证这次不会!”
我与江策日间赶路,夜间在客栈落住,花了六日的路程,终于赶到了福州,我们这回来福州是要调查杜家掌门人杜擎暴毙一案。
因为我失忆的缘故,江策不得不勉为其难地为我普及了一些江湖中人尽皆知的事。
自武林划分正邪二道以来,正道向来以少林武当马首是瞻,奈何少林一心向佛,武当又潜心修道,二者不过是虚名而已。久而久之,衍生出了武林四大世家。
徐州方家,江宁江家,福州杜家,太原林家。
江策乃是江宁江家的掌门人,而死了的那位则是福州杜家的掌门人杜擎。
半月前,杜擎一夜暴毙于风波林,致命伤为“斩云掌”,而这‘斩云掌’中正是杜家的独门绝学,他这一死可谓蹊跷。杜擎的身份在江湖举足轻重,他一死,江策身为武林盟主自然不能坐视不理。
由于半月前江策杀了青城派掌门及其师弟一事算在我头上,如今正道中人各个将这桩命案栽赃在我身上,险些要开铲魔大会干掉我这魔头了。
不过江策也想不通,二十年前,杜擎以一招“翻云覆雨”成名江湖,这‘斩云掌’中正是杜家的独门绝学,怎会如此轻易就教人学了去,造诣竟还盖过了杜擎本身?
江策对我知根知底,自然不会怀疑是我动的手,他认为凶手能窃得“斩云掌”,极有可能是祸起萧墙。
如此看来,凶手非但造诣深厚,还绝顶聪明,以‘斩云掌’为杀招,为整桩凶案掩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面纱。
当晚,我们赶到福州,准备找一家客栈落脚。谁知掌柜的一见我们要住店,就道:“实在抱歉了二位,小店只剩下一间客房了。”
“就一间?”江策扭头询问我的意见,我心道他一个大男人怎的如此矫情,我俩山洞都一起睡过了,不过是一间客栈,怕甚么!
我道:“就一间!”
小二领着我们到客房,我叫了一桶热水扒光了就往里边跳,一个人洗得不亦乐乎,江策忽然背对我道:“你先洗,我去杜家一趟。”
我道:“不是说了明日再去么?你这么晚了过去人家一个寡妇在家,多不合礼数龋
他道:“我不过是去暗访一趟。”
我想说我也要跟着去,可想了想江策内伤未愈,还要带上我这个包裹,待会暗访不成反倒被逮住,那这脸可就丢大发了,于是道:“那你早去早回。”
“好。”
江策应过之后便走了,我将自己收拾干净滚上床睡了。不知过了多久,正睡得迷迷糊糊间,有个人推开房门坐到床前,伸出生着薄茧的指腹轻轻在我脸上摩挲,我脸上一阵发痒,不由一把抓住脸上那只手,睁开眼来。
江策正坐在床前目不转睛地望着我,见我忽然醒来面上露出些讪色。
我心道盟主你偷吃了本座那么多次豆腐,终于被逮了个正行罢?我道:“你在杜家查探出甚么来了?”
他道:“不曾。”说着,就要装作毫不在意地将手收回去。
我见他一副扭扭捏捏的模样,道:“大男人偷偷摸摸地像甚么样子,大方点!”说罢,拉着他的手到我脸上抚摸。
江策怔了一下,收回手道:“哎,你的心思我是越来越猜不透了……”
江策说的这句话我委实听不明白,我不过是叫他做事大方点,还能有甚么心思?
我思忖了一会,道:“你数次救我于危难,我心里十分感动。你的心思我也是明白的,只是我如今失忆了,一切都是从头开始,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些时间,一切顺其自然,你说成不?”
江策叹息一声,道:“就照你说的办。”
26
26、第二十六章 冤家路窄
翌日,江策将自己收拾一番后就去了杜家,我在脸上作了一番掩饰,佯装成他的随从一道去了。
杜夫人一听江策前来拜访,亲自出门迎接。这位杜夫人年轻时曾是正道的第一美人,如今虽是半老徐娘,身着素缟,但仍是掩不住的娇如红杏,艳如桃李。
杜夫人一见江策就落下两行清泪,声泪俱下道:“先夫遭奸人所害,含恨离世,还请江盟主查出真凶,为先夫讨一个公道。”
江策连忙扶起她的身子道:“江某得知杜掌门遇害的消息后,马不停蹄地赶来福州,谁知在半路遭逢魔教教主萧定,江某怀疑此事与他脱不了干系,一路跟踪,还是让他逃脱了。未能赶来送杜掌门最后一程,还请杜夫人原谅。”
我听得喉咙一腥,险些吐出一口血,感情本座就是你的挡箭牌,放哪挡哪……
杜夫人道:“江盟主为了先夫的案子奔波,妾身已感激涕零,江盟主无需介怀。”
从杜夫人身后步出一名约莫二十出头,样貌俊逸的男子,上前抱拳道:“在下曜日山庄总管周远山,江盟主与夫人在门口站了许久,不如先进内堂再叙。”
杜夫人闻言,连道失礼,将江策请入了曜日山庄。
我们先到后山的杜擎墓前上了香,随后一行人移至内堂,江策问起杜擎死前的情形,杜夫人便将各中情形一一说来。说起杜擎死的那一夜,曾有人送来一封信,约杜擎晚上亥时去城外风波林见,杜夫人见来着不善,便劝杜擎莫要前去,杜擎不听,一去就是彻夜未归。
杜夫人一宿未眠,翌日便差人前去风波林寻找,怎料得知的却是杜擎已经驾鹤归西的消息。
提及当日种种,杜夫人仍是止不住的泪水连连,泣不成声。总管周远山在旁劝道:“夫人,逝者已逝,生者如斯,您怀了掌门的孩子,千万要保重自己的身子。”
江策一惊,道:“夫人怀了杜掌门的骨肉?”
杜夫人闻言,泪水这才止住了些,道:“是,已有两个多月了,老天垂帘,为先夫遗下一个孩子,延续杜家香火。倘若不是这个孩子,妾身早已绝食殉节,随先夫去了。”
江策道:“如此杜夫人更要保重身子了,江某必定尽快查出凶手,以慰杜掌门在天之灵。”
杜夫人道:“谢江盟主关心,妾身一定铭记于心。”
江策与他们聊了一番后,便拉着我回客栈从长计议了。杜夫人一人守着一个曜日山庄,我与江策两个男子住下怕外边风言风语,说了闲话。
我道策:“这桩案子你怎么看?”
江策道:“我们在崖底耽搁了不少日子,未曾赶上杜掌门下葬,这死因如何也是听他人说,不好下论。”
我道:“那你的意思是想见见杜掌门的尸体了?”
江策颔首。
我道:“那我们就去挖开坟墓瞧瞧。”
江策道:“杜掌门已入土为安,我们若是挖开他的墓,恐怕打扰了他的安宁。”
我道:“他自然也想早日抓住杀害自己的凶手,你为了查出凶手挖他坟墓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定然不会怪你的!”
江策又道:“你适才也见到了杜掌门的坟墓,我俩若是去挖,恐怕到明早都挖不到。”
这杜擎的坟墓确实造的十分奢侈,我俩就算呕心沥血地挖到了杜擎的棺材,棺材上了钉,我俩要撬开也要花不少时间,更无论他坟墓上还有几人轮流守着。
我道:“你受了伤,我们也不要去做这体力活了,这里有正义教主的分坛,我去找几个好手让他们帮我们挖。”
江策道:“正道的事,怎能麻烦你操心。”
我道:“正道死了几个人我才不管,不过既然是你的麻烦,我总不能坐视不理,你一句话,要还是不要?”
江策默了一会,道:“要……(v?v) ”
江策话一出,我立马跑到分坛下令,裴逍得了我的叮嘱正守在分坛,我话一放,其他的便由他来代劳了。
是夜
月明星稀,凉风习习,宜作案!
我带着数名帮好手跑到曜日山庄后山,因为怕江策又不知哪里会冒出些飞醋,所以未曾让裴逍跟着。
杜擎的墓前有两名男丁正守着,我瞧了瞧风向,放心地撒了一把迷|药过去,两个男丁登时晕了过去。
“上!”我一声令下,身后冲出去数名好手,埋头挖坟,手法熟稔,手段干脆。我与江策悠闲地蹲在边上嗑瓜子,等他们刨开坟墓,又撬开杜擎棺材后,江策这才上前查看。
尸体放了这么些时日,已经开始发出腐臭,我瞥了一眼,就捂着鼻子扭过眼道:“如何?”
江策扒开杜擎衣襟瞧了瞧道:“杜掌门身上中的确是‘斩云掌’。”说罢,他扒光了他身上的衣裳,细细检查伤口。
待江策检查完毕,我将剩下的烂摊子丢给几个下属,衣袍翩翩地跟着江策走了。回了客栈,我兴致勃勃道:“如何,今日有何收获?”
江策道:“杜掌门身上确实中了‘斩云掌’,虽然是致命伤,但这‘斩云掌’的功力并不深厚,说明凶手内功并不深厚。杜掌门身上又无其他伤口,我怀疑他是让人事先下了药。”
我道:“能给杜擎下药,不是曜日山庄的奴仆,就是他身边极为亲近的人了。”
于是,我俩开始讨论究竟是谁最有这个作案动机。最值得怀疑的,就是杜擎那位风华正茂的夫人阮翠云,而最不可能暗害杜擎的,亦是他那位夫人阮翠云。
十年前,杜夫人曾为正道第一美人,她与杜擎成亲时不过二十出头,而杜擎已是不惑之年,明眼人都能瞧出她是为了杜擎掌门人的这个位置,而并非杜擎这个人。她嫁与杜擎六年,未曾诞下一子,倘若杜擎死了,她成了寡妇,必定守不住这偌大的杜家,那她处心积虑地嫁与杜擎岂不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更何况如今她怀了身孕,若是诞下一子,那这杜家往后还不是她的天下?她又何必跟自己过不去!
江策开始着手调查杜擎一案,我无所事事,听闻附近有家回春酒楼做出的清蒸鲈鱼十分鲜美,便拉着江策前去尝鲜。
这回春楼宾客如云,我们候了一炷香的功夫,这才得了二楼一个位置,点了一盆鲈鱼,几道小菜,一壶小酒。待清蒸鲈鱼上来后,我一尝,不愧是这回春楼的招牌,鱼肉滑嫩、味道鲜美,我大快朵颐,吃得不亦乐乎。
正是尽兴,忽然从边上冒出几个人,一脸惊喜地朝着江策道:“江盟主?”
我扭头一瞧,面前站着一名绿衣的少年,一瞧就是名门子弟,身后还跟着几名随从。这少年生得十分出色,粉雕玉琢,眉目生动,一双大眼水汪汪的,我不由多看了几眼。
江策见他怔了一下,随即噙笑道:“原来是方贤侄,你不在云净山庄怎么会在这?尊父近来可安好?”
云净山庄?这名字为何如此熟悉?
少年笑着道:“我爹带我来送杜掌门最后一程,他有事前几日回去了,我见福州好玩就多停留了几日,明日也准备回去了。”
江策噙笑道:“原来如此。”
少年道:“我们等了好一会儿了还没有地方坐,可以跟江盟主一同坐么?”
江策道:“自然,不胜荣盛。”说罢,望了我一眼,道:“啊二,这天色不好,过一会怕是要下雨了,我出来时未曾关窗,你回去瞧瞧。”
哈?我就不提这阿二这名字有多二了,如今碧空万里的,哪有半点下雨的迹象?就算我佯装成你随从的模样,你也不能拿我当小厮来使唤龋
我心里不悦,坐着未动。岂料江策脸色沉了下来,道:“怎么,我平日待你太好,如今都使唤不动了?”说罢,还在桌下踹了我一脚。
我心说这江策为何一门心思地想赶我走?莫非……这少年是我的老相好?我连忙扭头望向少年,对方也好奇地一眨不眨地打量我。
我冷汗津津,正想道:“我这就回去关窗。”谁知少年忽然一把拉住了我,脸上惊疑不定道,“你……你是萧定?”
本座脸上点了这么多痣,添了两块面疙瘩你都能认出来?我立马道:“你认错人了!小人是江盟主的随从阿二。”
少年激动了,道:“我不会认错,你就是萧定!”
少年的嗓门太大,旁边已经有不少人投目光过来,我连忙捂住他的嘴道:“你真的认错人了。”
“唔……唔……我没有认错……唔,你就是……萧……定……”少年用力扒开我的手,道:“你额头上有一道疤,因为我才受伤的,我怎么会认错?”
我额上的伤口?我额头上的伤疤不是强|暴云净山庄少庄主未遂留下的?虽然伤口愈合了,但还是留下一个淡淡的疤痕,不仔细瞧是瞧不出来的。我脑子忽然一个机灵,抽着嘴角问江策:“你叫他方贤侄,哪里的方贤侄,他叫甚么名字?”
江策沉着脸道:“云净山庄少庄主方天生,徐州方掌门之子。”
我垂死挣扎道:“不是……我那啥……未遂的那个……对吧?”
江策一脸沉重的颔首:“正是。”
呜呼,哀哉!本座这会回去关窗还来得及嘛!
27
27、
我拔腿就跑,谁知让方天生一把拉住了,道:“你为甚么一见到我就跑?我有这么吓人么?”
我斟酌了一下,准备走坦白从宽路线,道:“方少爷,既然你认出来了,我就不跟你装蒜了,作出那种事是我对不住你,我一时糊涂,猪狗不如,你就瞧在我已经吃了苦头的份上,放过我罢。”
方天生皱眉道:“你在说甚么胡话,你知道你一走我有多担心么?你说了会来找我的,为甚么没来找我?”
我心道本座强|暴你未遂,再去找你不是欠揍嘛!“方少爷,我做了那等丧尽天良之事,恨不得一死以谢天下,哪还有颜面去见你呐!”
方天生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登时变得湿漉漉的,瞪着我道:“我跟你说了我叫天生,你还一个劲的叫我方少爷,是存心疏远我么?你说了来找我也没有来找,你还问江盟主我叫甚么名字,你是不是连我是谁都不记得了?你说会来找我,是敷衍我的不成?”
我让方天生的态度搅得十分糊涂,试问哪有被强|暴者一脸不高兴地问施暴者你为何不叫我的名字,你为何不来找我?这小少爷是不是让我施暴未遂不过瘾,想让我得逞一回?
我道:“方少爷,在下晓得错了!我猪油蒙了心,丧尽天良,猪狗不如,居然对你有不轨的心思,我这不是遭了报应了么?我让你的花瓶砸中了头,昏迷了三天三夜,醒来都失忆了。你就瞧在我遭到报应的份上,放我一条生路吧!我保证从此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了!”
方天生闻言一惊,道:“我用花瓶砸伤了你的头?你胡说甚么呢?我怎么会去伤害你呢,你额头上的伤不是为了救我磕在石头上砸伤的么?”
我一怔,呐呐道:“你再说一遍,我这额头是怎么伤的?”
他道:“我从马上摔下来,你为了救我所以一起跳下马来在石头上磕伤的取!
我惊道:“不是我强|暴你未遂,让你用花瓶砸伤的么?”
方天生的脸忽地红了,跟煮熟的虾子似的:“你……你胡说甚么呢你……你……你对我有那种心思?我……我……其实我……你救了我的命,我怎么会用花瓶去砸你呢?”
我觉得这其中必有隐情,道:“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好好跟我说,我如今失忆了,有人跟我说我额头上的伤是强|暴你未遂,让你用花瓶砸伤的!”
方天生听我这么一说,气道:“谁这么胡说八道?你千万别信他们的话!”随后,他开始向我整件事的前因后果。
话说这方天生乃是徐州方家方凛之子,自幼娇生惯养,家人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他认为父母太过小瞧自己,离家出走,准备到江湖上闯荡一番大事业。
谁知出师未捷身先死,一出家门就碰上一个穷凶极恶之徒,非但对他动手动脚,还想行不轨之事。他是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正是这千钧一发之际,英明神武、气度非凡的本座从天而降,帮他打退恶人,还送他回家。
途中他一个疏忽打了瞌睡,落下了马儿,本座为了保护他毅然从马上跳下,搂着他在草地上咕噜咕噜滚了一大圈,脑袋好死不死地嗑在石头上,光荣负伤了。本座顶着一脑袋的血送他回家,承诺会再回去找他后就走了。
一别数月,他是日也盼,夜也盼,只希望本座能在百忙之中去看他一眼,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日日思君不见君。本想跟随父亲到福州散散心,怎料竟能在福州遇到本座,真是天赐的良缘,地造的一双!
我得知前因后果后,暗暗咬碎了一口银牙。林郁文呐林郁文,你可真是插得一手好刀,本座到底哪得罪你了,你要如此冤枉本座!
我一把握住江策的手,道:“阿策,你都听明白了?我是被冤枉的,甚么风流成性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