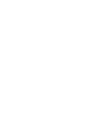段时日……”
☆、第 四十六章 ?谈话
季临川的话音骤止,有如看见牛头马面索命而来,一双眼惊恐睁大,身子抖动不止。他带着绝望阖上双眼,瘦弱的手攥紧了晏苍陵的胳膊,根根青筋暴凸而起:“时隔多月,我仍会在梦中惊醒,想起那时的场景……那个人狰狞的笑容……那把划在我手脚筋上尖刀……”
“不!别说了!”晏苍陵打断了季临川的喃喃自语,掰过他的身躯,迫使他看着自己,“z涵,莫想了,那只会于有损你身心。你当出外走走,去看看别的,想些别的。”
季临川双睫一颤,一句话哽在喉头,难上难下,热意从眼眶而出:“你不好奇么?我的过去,我为何会成如今这样。”
“我为何要好奇,”晏苍陵不答反问,“你过去如何,你为何变成如此模样,又有何关系,你依旧是你,依旧是季临川。人该登高望远,而非倒退回望,过去一切皆是浮云,不过是被狗咬了一口罢了,你怕什么,莫非你还要怕一只狗不成,若是如此,那我便瞧不起你了。”晏苍陵执起季临川的手,轻轻地握在手心里,手指顺着那锭木银走过,“你曾告知过我,前路难行,则披荆斩棘。而今恐惧笼于你心,你是否能披荆斩棘,将其从心底摒除,唯有靠你自己。这一条路,我无法相陪,只能倾注力量于这锭木银之上,望它能助你而行。”
“木银。”季临川心头一跳,低首看去,只见手心里的红绳亮得刺目,有如热血燃烧,燃起希望,倏尔间心胸开阔,浩气翻涌,“我会尝试着走过去,若是不能……”
“甭说什么能不能,一定能!”晏苍陵包紧了季临川的手,温暖得近乎让他窒息,“你也不想你爹担忧罢。”
“我爹……”季临川身子一震,眼底又笼上了哀色,“他不会懂的,不会懂的。”他反复地说着不会懂,却不知究竟不会懂什么。晏苍陵也不知实况,唯能握着他的手,字字句句铿锵有力:“不论他懂不懂,至少,我懂。”
霎那,心旌神摇,季临川眉间的哀色有如被狂风席卷,过后一片宁静,嘴角划开一抹笑容,如四时花开,常开不败:“好。”没有什么词汇,比之一个“好”字来得简单,季临川撑身而起,张开双臂,竭尽温柔地拥上了晏苍陵,“来,给我一个拥抱,便当庆贺我同过去告别。从今日起,我会尝试着遗忘过去,正视恐惧。”
晏苍陵笑了,将季临川紧紧地拥入怀中,给他所有热量。这一个拥抱,无关情爱,只与勇气有关。
季临川是坚强的人,晏苍陵始终相信,他可以恐惧数年,却可在一瞬间站起,只需一句简单的鼓励,一个朴实的承诺,便能让无助的他张开双翼。
松开怀抱时,季临川头还有些晕眩,险险地扶住晏苍陵:“我一旦心病生,便会如此,你不必担忧。”他试图安慰晏苍陵,不想他越是如此安慰,晏苍陵越是不安,还弄得晏苍陵神经兮兮的,唤王大夫给他开了一对没甚用处的药。
“成了成了,你要将我弄成药罐子不成,”季临川横了晏苍陵一眼,将那些有的没的药推拒开来,“我一会儿歇会便好,不必担忧。”
“z涵,你若有何需我相助的,只管说,我定会助你。我只求你一时,”晏苍陵顿了一瞬,目光直白地盯着季临川的眼瞳,深邃地似能将人吸食进去,“你若有事,定要告知我,不要瞒着。”
“嗤,”季临川笑了出声,“我能有何瞒着你。方才我不是想告知你,么,是你不愿听。”
晏苍陵摇首:“你今日说,不代表明日不会瞒。今日若非我见着你的不对,你岂非会……不说了,你立誓便是。”
季临川咂了咂舌,这人好生霸道,自个儿还未应呢。
“z涵?”晏苍陵扬了一声,季临川叹息一声,乖乖地立了誓。
晏苍陵绷紧的线条,徐徐舒展开来,他会心一笑,给季临川喂了一口水,岔开话题道:“也不知王斌同你爹怎样了,该不会打起来罢。”
“说到这事,”季临川放下手中茶盏,视线凝注在晏苍陵身上,一字一顿沉得如同来自深渊,“我还未问你,关乎我爹之事呢。”
晏苍陵心头一跳,面上仍故作从容镇定:“你爹何事。”
“你要我有事,都不瞒你。那你呢,你可能做到事事皆不瞒我,老实告知我?”季临川不给晏苍陵辩解之机,继续念叨,“人总说待人以诚,朋友当是如此,情人……”他一顿,脸上生起淡淡的红晕,“情人亦是如此,若朋友时都隐瞒彼此,情人的话……嗯,总之,你还要瞒着我么。”
看绯色爬上了季临川的耳尖,晏苍陵又惊又喜。季临川主动提及“情人”二字,可是他承了自己之意?心头涌上喜悦,晏苍陵握住了季临川的手,支支吾吾地道:“z涵。我……你……”
“我什么,你什么,”季临川嗔了一句,将他的手打开,偏移了头借风散去面上燥热,“你若再不老实说,我连朋友都不同你做。”
“说……”晏苍陵叹息,论他在他人面前如何英明神武,对上季临川那对真诚而无暇的眼,他便成了一只软猫,“唉,你想知晓什么。”
“你在临行前,问我如何对付固执之人,这固执之人说的可是我爹?你为何要如此做。尚有,王斌当真是替他大哥报恩的么,为何言辞间倒像是替他自己不平。”
一口气抖出如此多的问题,晏苍陵倒真不知该先回复哪一个了。一口叹息在胸前迂回婉转,最后吸入口中,化为了一句句肺腑之言。他毫不避讳,将自己所有的算计一一道出,连同王斌之事的缘由也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话尽之后,他毫无愧疚之色,反而挺起了背脊,端肃容色,正视季临川颇为不悦的目光――到底他害得季崇德背负了谋逆之罪,身为季崇德之子的季临川,自然会不快。
晏苍陵本准备好了一番义正言辞的话语,想劝动季临川,不想季临川却自眉间展露了笑意,轻轻拍了拍晏苍陵的肩头道:“你辛苦了。”
没来由地道出如此一句话,晏苍陵尚有些发懵:“你……不怪我?”
“怪你?嗯,我当是要怪你。怪道我爹见着我会目光躲闪,说话支支吾吾,原他是背负了谋逆之罪,生怕我担忧。”季临川不怒反笑,“但我却不得不夸赞你一声,此计用得甚好,我甚是赞赏,若非有此妙计,只怕爹还心挂朝廷,落于那人,呵,之上。”
晏苍陵心头一跳,听罢季临川这话,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可哪儿不对劲,却道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索性将其瞥去,问道:“z涵,”他握着季临川的手,将自己滚烫的热意涌上季临川的掌心,“你当真不怪我?”
季临川摇了摇头:“不怪。”他顿了一瞬,猜到晏苍陵要问什么,敛下了双目,目光晦涩不明,“不要问我为何明知谋逆是大罪,却不怪责你,我不想道明。我只问你,慕卿,你是否真的有心天下。”
晏苍陵出口的话不需过脑,声声铿锵:“是!”
“可你知谋逆天子,乃是死罪?你却还是要拖我爹下水,有何用意。”
“有何用意?“晏苍陵苦涩一笑,”我能有何用意。而今天下世道黑暗,你爹被小人诬陷,天子听信谗言,便将其流放远处。朝廷局势一眼可见,你以为你爹还能回朝廷么,不。他回不去,非但是小人不容他,天子不在乎他,尚有他自己,心存护着天子之心,终有一日会被小人利用。你爹是骨鲠之臣,奈何遇上了不适合他的君王。他当是侍奉明君,替明君抛头颅洒热血,而非伺候一昏庸无能之帝,成为他人手下的棋子。我谋逆天子固然死罪,可我一心为的不是天下,而是百姓。是百姓辛勤耕种,赏我一口饱饭,是百姓织布,赐我一身衣穿,食之百姓,用之百姓,我有何理由弃他们于不顾。这天下不当是天子一人的,当是百姓的。至于你爹,只是还未开窍,我相信终有一日,他定能明白,我们的用心良苦。我虽害他无处可归,可我若不如此做,谁人知晓他可会死在配所,谁人可知你还可能同你爹相遇。”
季临川笑意晏晏,连外头的花都娇羞了颜色:“你说得甚是在理。但我身为亲儿,总不该瞒着亲爹的不是?”
晏苍陵方酿起的雄浑气势便如开闸洪流泄了个干干净净,蔫蔫地扫着季临川:“z涵,你当真如此狠心,让我被你爹抄着刀子砍么。”
“嗤,”季临川笑着摇首,“你若不想我将你的事抖出,便应承我五件事,若能做到,我会替你在爹面前说好话。如若不然,便等着挨我爹的刀子罢。”
“什么事?快说。”晏苍陵眼珠唰地亮起。
☆、第四十七章 ?承诺
“我要你所做之事极其简单,于你而言兴许不过是动动手指头,挥挥手让他人去办便可。但这些事说来容易,真正能做到底,却是很难。”
“z涵你便说罢,究竟何事。若在我能力之内,我定应承你,只要你信我。”晏苍陵信誓旦旦地道。
“我并非不信你,而是不知你是否能坚持到底,”季临川轻轻抿唇,淡然地化开一抹笑意,反手覆上晏苍陵的手,将他的手蜷成一个拢不紧的拳头。季临川笑着翻过晏苍陵的手掌,将他拢成拳头的手指一根一根松开,每松一根,便续上一句话。
“我要你替我做的第一件事,替我寻到家人的下落。”一根手指被轻轻掰开,却在被绷直之刻,便被季临川的手握紧,颤抖的烫意交织着苦涩与痛苦,顺着指尖,漫到了晏苍陵的心底。
晏苍陵不假思索便应了此事,另一手拍上季临川的手背,柔声细语地安抚:“此事不消你说,我亦会帮你。原先我未曾确信你的身份,是以未能多加深入细查,生怕做白功。”
“嗯,”季临川牵动嘴角,温和笑道,“我知晓,劳烦你了。”
晏苍陵颔首,不多同他客套:“那第二件呢。”
“第二件事,”对着晏苍陵的眼底倏尔涌上一股滔天巨浪,翻云覆雨间气吞山河,季临川猛地抬首,惊涛骇浪瞬间将晏苍陵习卷,气势磅礴得令人窒息,“我要你,诛!庸!帝,谢!天!下!”
气势雄浑,遒劲有力,连他清瘦的手指上都凸起了根根青筋,晏苍陵都不敢想象,这竟是从季临川身上而发,无边的惧意涌上,让人胆战心惊。
“z涵你……”带着疑惑开口,却被季临川拂手堵下余下的话。
“为天下,为百姓,为我……”季临川顿了一瞬,续上了一个“爹”字,“这样的理由可足够?”
“够了,”晏苍陵划开笑容,“只需为天下三字,便足以让我颠覆苍生。”
季临川同他对视一笑,将他第三根手指掰起,自己的五指也随之握上那根手指,将心中一片热意过度到晏苍陵的手上:“待你君临天下,我要你不忘昨日之耻,不忘青云之志,不忘百姓养育之恩。忧百姓之忧,乐百姓之乐。行则端其身,言则正其语,时刻铭记民贵君轻。”
晏苍陵另一手包裹住了季临川的手指,五指从季临川的指缝间穿入,同他全指相贴,晏苍陵专注地看着季临川,一字一句敲金击石:“我应承你。他日君临天下,定不忘今日之誓,心挂百姓,爱民如子。”
季临川的笑意漫上了眼角眉梢,一窜绯红也悄无声息地爬上面颊,他偷偷地瞟向晏苍陵的肩头,那儿宽厚踏实,甚有安全感,若是靠上去,当是舒服极了的――如是想着,他便这么做了。近乎是下意识,他的头便枕到了晏苍陵的肩头,脑袋感觉到热意时,他还红脸地被自己所为给吓着了,但当把脸皮扯厚了后,他便放大了胆子,调整了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姿势,笑眯眯地拍了拍这个“靠枕”,夸道:“还不错,尚可用。”
“……”晏苍陵本来乱跳的心头,便被这一声浇了一盆冷水,止住了跳动。
“嗯,方才说到第几了,”季临川挪了挪自己的头,“嗯,第四,”他又掰起晏苍陵的手指,“我要你,嗯……对我爹,嗯,对我好些。我爹年纪大了,加之受了如此多事,心力交瘁,不宜再受刺激。你若想我同你好,便先对我爹好,少同他吵,不然连我都帮不着你。”
“好好好。”晏苍陵无奈,此刻他深觉自己便如同一个丈夫,在听着自己妻子的唠唠叨叨。嗯,妻子?这个意识扑入脑海,让他脑中一片空白,只留得一幕红衣软帐,龙凤香烛,两人相吻相缠……
“哎哟!”自己出口的一声大叫,生生将自己吓得从幻想中走出,晏苍陵回神时,发现季临川正瞪着一双不悦的眼看着自己,晏苍陵哭丧着脸看自己的胳膊,成,季临川从撞自己,改成了捏自己胳膊了。
季临川也为自己的所为找好了借口:“你皮厚。”
“……”晏苍陵放弃了同季临川争执。
季临川摆正了容色,将晏苍陵最后的一根手指掰起,直直地对着晏苍陵的目光:“最后一样,我要你方才所应承之事,皆要说到做到。”
无需说太多的话语,晏苍陵回以一笑,浅淡地应了一个字:“好。”一字铿锵而落时,他人已经站了起身,走到一旁的书案上,挥斥方遒的笔触点染黑墨,狼毫一挥,条条清晰的话语印入纸张之上。他将那张写好的纸拿起,满意地纵览一遍,点了点头,将其送到季临川的面前:“z涵,你瞧,我写的可有遗漏。”
“呀?”季临川讶异接过一看,心头便浮上了暖意,那张纸上,将方才他所说的五点,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末了还多了几句立誓的话语,一句一句皆出自真心,笔触的锋利,力透纸背,足见立誓人的真心诚意,“慕卿……”
“嗯,确认无误了?”晏苍陵朗笑地抄过那张纸,快步走回书案前,取过红印将自己的大拇指按上,轻一碾压,再将染红的拇指深深地印在纸张上的落款之处。
季临川乱了一片的心,醉在了那张刻满真心实意的纸里,若非当真将自己放在心上,晏苍陵一有如此身份之人,又怎会委屈自己,应下如此多事。“嗯,嗯……”嗯了半晌,皆续不出一句合宜的话,季临川唯能接过晏苍陵递来的纸笔,在落款边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以作见证。
晏苍陵再将写好的纸张放入信封封好,递给了季临川:“此信物交由你保管,若他日我有一事未能做到,你则以此物公于天下,让我受尽天下的唾骂。”
季临川会意一笑,小心地将其放入自己怀中:“我相信你可做到。为了回报你的付出,我定想法子劝服我爹助你,我亦会努力走出过去阴霾。今后你若有需我相助之处,定要告知于我。”
晏苍陵会意,颔首一笑,只将两人的手指根根贴近,连一丝空气都无法挤入。他试探地低首,小心地将自己的头慢慢靠向季临川,努力地将自己的唇往那如水般润泽的唇上贴去。
试探着,小心着,再到心头乱跳着……
他含着他的唇,轻轻地索取吮吸,温柔得不似接吻,而似在含着一块甜腻的糖,生怕含得重了,糖会化得只余满腔齿香,是以需得周全对待,轻柔舔舐,柔情似水。舌尖撬开了他的牙关长驱直入,相闻的呼吸萦绕鼻端,顺着缠绵的吻,顺着彼此的味道,入了心,生了根,抽枝发芽,长成以爱为根,以情为叶的参天大树……
而便在晏苍陵同季临川情意相交之时,京城内天色骤暗,乌黑卷云承着即将倾盆的雨,将京城一片压得昏黑。
轰隆!电闪雷鸣,炸开于云雾彼端,还在匆匆赶路的吴其康吓了一跳,赶忙撩开车帘,朝着赶马的几位亲卫扬上一声:“快些快些,进城去。要落雨了!”
这几位亲卫正是当日救下他后,一路护送他到京城之人,本来救下吴其康已是倦极,这日还带着吴其康连夜奔波到京城,早已累得受不住,眼底逝过短促的异色,其中一名亲卫懒洋洋地应了一声,便抽动马缰,朝前而驰。
入得皇宫,天色更暗,轰隆雷鸣声噼里啪啦作响,一达目的地,吴其康匆匆扶着车壁跳下马车,这时,马车没来由地一歪,他身子受撞,脚步一错,就歪歪斜斜地往一旁倒去。
“王爷!”亲卫快手扶上吴其康的胳膊,不想动作再快,吴其康怀中揣着的东西还是掉了出来――轻飘飘的落地,沾了一层的灰。
吴其康急忙站好,欲弯腰去捡,但一双手恭敬送来,掉出的东西便呈到了他的面前,正是那一份装着季崇德“罪证”的信封。
吴其康满意地颔首,扯过信封,估摸着摸了一下厚度,确信封口未被启封后,便将其出塞入怀中,大大咧咧地走了。
殊不知,前方他走的畅快,后方的亲卫便笑吟吟地从怀中取出了一封同吴其康此刻手中拿着的一模一样的信封,将信封拆开来一一阅览后,亲卫小心地将其放入怀中,若无其事地左顾右看,好似方才偷换信封之举同他无关。
天子为鼓励抓获叛逆之人,许以亲王郡王特例,若有必要,可离开封地,是以吴其康敢如此明目张胆的无视律法来京不是没有道理的。
吴其康掸袖整衣,在宦侍的带领下,入了朝殿,对着正中高坐上方的天子附身下拜:“参见吾皇。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天子――安天仁年近半百,因长年纵欲,被情欲毁了身子之故,他瘦得几乎不成人形,眼窝深深地凹陷进去,肌肉松弛,张口闭嘴间,下巴便有一层干瘪的肉抖动。他歪歪斜斜地依靠在龙椅之上,正是听朝议听得无聊之时,一听西平王要带着谋逆之人来朝相见,登时来了兴趣,双眼乍亮,挥手道:“来来来,带上前来给朕瞧瞧。”
吴其康心头一喜,以为得天子垂爱,能得封赏,遂膝行向前,将头伏得更低,敛下眼中对安天仁的憎恶。
看他如此乖顺,安天仁也乐开了花,同吴其康问了几句后,便直接问道:“听闻你抓获了一谋逆之人,不知是何人?”
“回皇上,此人正是前任兵部尚书,季!崇!德!”
☆、第四十八章 ?反诗
嗬!百官皆惊。一些同季崇德交好之人,齐齐对视,目中逸出不敢相信之色,季崇德是出了名的愚忠之臣,衷心护主,众人皆知,谁人会信他会反了天子。
安天仁亦是不敢相信,他虽将季崇德流放,但也是经过了一番考量,确信季崇德不会害自己,方敢如此做的,不然单凭季崇德所犯之事,他早悄悄地派人在半路将季崇德给杀了。
“季崇德……季崇德,不是在流放途中么。怎会谋反呢。”安天仁目光闪烁,怯怯地将目光放至朝殿下方的一人身上,那人恰是安天仁的床笫宠臣,七年前的刑部侍郎,如今的刑部尚书――王恩益。
王恩益长相阴柔,面若冠玉,以色媚主,但他能在宫中打滚多年,独占龙床之侧,爬至三品高官之位,肚里还是有些本事的,是以无能的安天仁常依仗他,凡事皆要过问他的主意。
王恩益单手一撩鬓发,一张看相人都说薄情寡义的双唇微微抿起,不发一言,勾唇看向吴其康,静待着他的下文。
安天仁接到王恩益的暗示,遂抵唇咳了一声,唤吴其康将季崇德之事道明。
吴其康当即将季崇德在配所期间,唆使犯人暴动,以及写反诗之事,一一道出,末了,还从怀中掏出一个信封,呈递给安天仁。
“皇上,此乃季崇德谋反罪证,当日众犯人也已证实了季崇德主使暴动之事,可惜微臣在押解季崇德的过程中,受他人追杀,季崇德亦被他人救走,微臣恐季崇德的谋逆之心因被微臣发现,背水一战率众前来京城,遂马不停蹄地赶来京城,给皇上您报信。“说罢,还将季崇德如何罪恶,如何害人之事,往夸张处说,声色并茂,让众人身临其境,仿若真真看到季崇德狰狞着脸,抄着手中大刀振臂一呼,带领众犯人烧杀掠夺的一幕。
安天仁听得心惊肉跳,心头有如万马奔腾,跳动不安,接过张公公呈递上来的信封,手都不停使唤地颤抖,尚需用自己的另一手,握上拆信的手,方能安稳地将信封打开。安天仁害怕忠诚于己的季崇德当真反了自己,季崇德为官多年,做到兵部尚书一席,手底下是有不少关系在的,加之季崇德掌管朝廷兵部大小之事,若是他当真有心皇位,只要运筹帷幄得当,皇位让主不在话下。
安天仁慌慌张张地从里头抽出了一张纸,强忍着颤意将其打开,目光却不予半点在纸上,反而看到王恩益之上,这是要王恩益拿个主意。
王恩益目中精光微闪,一手抚上鬓发,另一拢在袖中的手,悄无声息地做了一个斩头的动作。
安天仁眸光亮起,方将视线转于手中的纸上,方发现这纸张自己竟给拿反了,阶下百官双双眼直盯自己,他忙给自己寻台阶下,清咳一声,他肃整容色,将那张纸丢给身侧的宦侍:“你来念!”
张公公弯身接下,摆正了纸张,将内里的季崇德“亲笔所写”那首反诗一字一顿地念出:“西风相送烛光灭,难平抑郁是今朝。他日王恩平吾反,赤子反躬忠于桓。”
张公公放缓速度念颂之时,安天仁的目光扫到王恩益上,给王恩益使了数个眼色,盖因他听不出这首诗中的谋逆之意,但若公然问吴其康,未免显得自己太过愚钝。
张公公最后一字落下,王恩益也听出了其中的问题,双唇掀动,方想同安天仁道出其中问题时,吴其康便先识趣地开了口:“微臣斗胆,请张公公将本诗中的最末一字,连成一块儿读。”
张公公征询了安天仁之意,遂将那些字窜成一线,朗声道:“灭、朝、反、桓。”
声音一落,有如惊雷劈到百官头顶,百官皆惊,齐声抽气。连安天仁都惊得一屁股坐歪,差些从龙椅上滑下来。
“这……这这这,谋逆谋逆!来人啊,将季崇德抓回宫,不不不,见之便斩!不必审了!”不过一首反诗,便不经御史台查证,便定下了季崇德的死罪,若是季崇德在场,定会后悔自己为了维护天子而辩驳王斌之事。
私底下同季崇德交好的官员都垂下了首,暗中使着眼色,摆着手形,但却无一人敢上前去,给季崇德说上一句好话。安天仁因昏庸无能之故,这几年没少出现起义谋反之事,以致他常谈及“谋逆”两字色变。“谋逆”便如同他的逆鳞,谁人若抚之,则龙颜大怒,皆被处之。
王恩益嘴角挑起一抹笑意,带着赞许看向安天仁,不期然间递上了一眼秋波,将安天仁勾得心头乱颤,转瞬便将方才下的死令给忘到了北。
恰在安天仁被勾魂摄魄时,一人沉然出列,冷着脸拱手禀道:“臣有话要说。”
“嗯?”安天仁的调情被人打断,不快地射向阶下之人,但一看到出列之人的面孔,又堆起了笑意,“傅爱卿,不知你有何话可说。”态度好得方才那生死决断的昏君判若两人。
若说这傅爱卿究竟何人,朝廷内无人不知。他乃当朝皇后的表亲,为人耿直不屈,手里端着不少的关系在,平日里虽未对天子阿谀奉承,但他却深得天子器重。盖因他为人圆滑,知晓如何处世能拿道好处,上不得罪,下不惹怒,在百官中口碑极好,拥护者不少。为人也甚是公平,若有不能决断之事,定会寻他人相商。此人官拜御史中丞,权势不及御史大夫,却往内里说,御史大夫都得听他的话。而他姓傅,名于世,字长焉。
傅于世低低垂首,极尽谦卑――便是这样尊敬安天仁的态度,让傅于世深得安天仁的宠信。
“微臣认为,此诗谋逆之意仅是表面,但若去其表面,窥之内里,那其中道理则耐人寻味了。”
“嗯?”安天仁又再次看向了王恩益,目光闪烁不定,收到王恩益摆动的手势后,挥挥手道,“何意,快说快说。”
“微臣斗胆,可否请皇上派人将诗上语句分拆成字,分别写于不同的纸上,再将其打乱。”
安天仁不明所以,看王恩益点头后,应许道:“来啊,照做照做!”
张公公授意,当即唤人准备好了纸笔,提笔在一张张小纸片上写下诗句上的字,再将其打乱铺展到桌上。
“微臣斗胆,不知皇上可曾从中看出什么端倪。”
“什么端倪,”安天仁眉头一皱,只看到一堆乱糟糟的文字,密密麻麻地涌入脑海,能看出个什么东西来。但傅于世如此问来,他到底也得做做面子,给自己一台阶下,故作镇定地摸着下颔,眼珠子溜了一圈。
倏尔,一道灵光打入脑海,安天仁指着台上的文字,“这这这……”的叫唤不停,双手于纸片中乱摸,从中摸出了四个大字,平摊放好,当这四个字连成一块,顺成一完整的意思时,安天仁的脸上已骤起了滔天浪涌,目光犀利有如萃了剧毒,射向台下的吴其康。他扯过张公公手里的原诗,上下研读一遍,怒从心生,取笔纸上圈出了几个字,接着狠狠地将纸张一掷下地,方才的软弱之态荡然无存:“吴其康,你尚有话可说!”
吴其康被安天仁突然而来的怒气弄得不明就里,抿唇将牙一咬,噗地跪倒下地,咬牙切齿地问道:“皇上赎罪,不知微臣所犯何事。”
“所犯何事,所犯何事!”安天仁气得手指都在打抖,挥手让张公公拿起那四张纸片,“大声念!”
张公公打眼一望那四张纸片,登时吓得跳了起来,哆嗦着手将那四字拿起,看了吴其康一眼,颤声念道:“西、平、王、反。”
平缓的声音,却如一火药炸开了百官,方才还是灭朝反桓,而今却是西平王反,这究竟是怎地回事!
傅于世趁势而开腔,恭谨地俯首道:“皇上,方才微臣听闻张公公念及此诗时,便深觉不大对劲。一来,季崇德对皇上忠心耿耿,若真有反心,早早便在京城时,同手下里应外合,逼宫造反,为何还偏生让自己前往如此荒凉之地平白受罪,假使他是为了忍辱负重,防您发现,那另一件事,便让人怀疑了。盖因他被发配之地,地处南州,南州西面临山,西风拂来是无法吹入南州的,故而这西风相送,未免有些偏颇。”
安天仁瞪大了眼,顺着傅于世的话问道:“那何处的风,方是西风。”
傅于世垂首,始终进退有度:“这微臣便不知了。只是当年曾去过一次南州,大略知晓了那处的地理风貌。但微臣斗胆猜测,兴许这西风所指的并非真正的西风,而是人,而此人兴许同‘西’字大有关系――”一个“系”字被他吊其拖了一个长音,深有十足的怀疑味道,众人唰地将目光放置了吴其康上,目带审视。
“西风相送烛光灭,”傅于世将这话一字一顿地顺道,“为何西风一送,烛火将灭。烛光灭常意寓风烛残年,西平王正是年少有为之时,那这烛光灭意寓何人?”
“岂有此理!”安天仁拍椅站起,怒发冲冠。他因纵欲过度之故,平白比人老了数岁,每每对镜而望,他总产生自己将飞天而逝的恐慌。以致日日夜夜派人去寻长生不老之药,渴望与天同存。若说这有人谋逆是他的逆鳞,这年之将老,便是他心中的那根刺!而今这首诗,却拔了他心口的那根刺,血液喷涌间,将他的杀意一同冲上头顶。
“来啊,拿下拿下,通通拿下!”
拿下?拿下何人?
☆、第四十九章 ?逆转
大内侍卫皆揣摩不透安天仁的意思,这拿下,是要拿下写反诗的季崇德,还是同反诗中内容大有关联的吴其康。
傅于世冷哼一声,拂袖便替安天仁道:“还愣着作甚!还不速速拿下叛逆的西平王!”
喝!心头明灯一点,朗声冲顶,唰唰几下,那些侍卫便如龙而